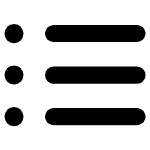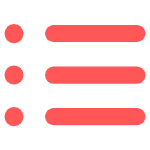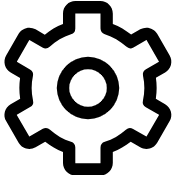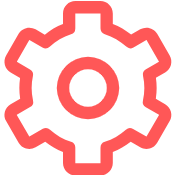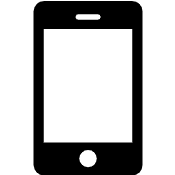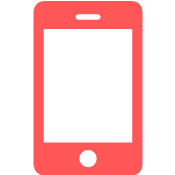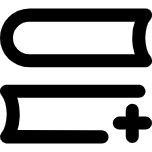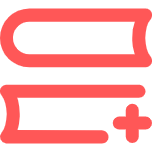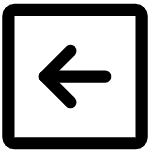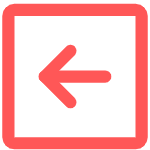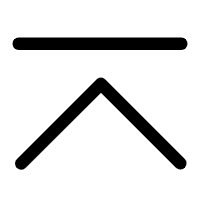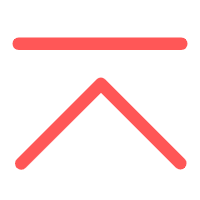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71章 猗兰清音
宣德西年的秋光,透过乾清宫高阔的雕花长窗,在光洁如镜的金砖地面上投下斜斜的、温暖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新贡秋菊的冷冽芬芳,与御案上徽墨的沉郁香气交织。朱瞻基端坐于宽大的紫檀木御座之上,并未如往常般埋首批阅奏章。他面前,置着一张通体乌黑、木纹如流水般细腻的古琴。琴身微光内蕴,七弦紧绷,散发出岁月沉淀的温润光泽。
他修长的手指悬于弦上,骨节分明,指腹带着常年握笔、挽弓留下的薄茧。殿内侍立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瑾、内阁首辅杨士奇、次辅杨荣等几位重臣,皆屏息垂手,目光或落在琴上,或恭敬地垂视地面,静待着帝王指尖流泻的天音。皇帝雅善音律,群臣皆知,但今日宣召赐听,显然别有深意。
指尖轻轻落下,拨动宫弦。
“铮——”
一声清越悠远的琴音,如同幽谷中第一滴清泉坠入深潭,瞬间打破了殿宇的沉寂,荡开层层涟漪。
朱瞻基并未疾奏,指法舒缓而沉凝。琴音初起时,带着几分孤寂的寻觅,如同空谷足音,在寂寥的山野间踽踽独行。秋风掠过枯草的萧瑟,寒露凝结于兰叶的清冷,仿佛都在这低徊的音韵中流淌。渐渐地,那寻觅的孤寂中,透出一股难以摧折的韧劲。琴声转承,变得舒缓而从容,如同幽兰于无人深谷悄然绽放,不因无人欣赏而减损半分芳华,自有其高洁之姿,清雅之韵。它不争群芳之艳,不畏风霜之侵,只将一缕若有若无的馨香,默默播撒于天地之间。
琴音渐入佳境,愈发空灵澄澈。指尖在七弦间游走,勾、挑、抹、拂,行云流水。那幽兰的意象愈发清晰,不再是孤芳自赏,而是以其坚韧与芬芳,无声地吸引着、召唤着同具慧眼、共秉清操的君子。琴声时而如清风拂过兰叶,沙沙作响;时而如明月映照花影,皎皎生辉;最终归于一片平和淡远,余韵悠长,仿佛那幽谷兰香己弥漫天地,沁入心脾。
“猗兰……” 当最后一个泛音袅袅消散于殿梁之间,杨士奇低低喃语,眼中闪过明悟的光彩。此乃托名孔圣所作的《猗兰操》!陛下以此曲相召,其意昭然!
朱瞻基双手轻轻按在犹自微颤的琴弦上,止住了余韵。他抬起头,目光扫过阶下诸臣,清朗的声音在寂静的大殿中响起,带着琴音般的温润与不容置疑的力量:
“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此《猗兰》之操,圣人所叹。今朕以此曲赐予诸卿,非独赏其清音。” 他微微一顿,目光变得深邃而恳切,“朕望诸卿,为国之幽谷!明察秋毫,善辨贤愚。凡有才德之士,无论出身寒微,或沉沦下僚,或隐于山林,皆当悉心访求,竭力举荐!使其才得展,其志得申,如幽兰得遇清风明月,芳泽播于庙堂!荐贤为国,此乃股肱之臣第一要务!朕之江山,赖贤才而固;朕之盛世,因群贤而兴!”
“陛下圣明!臣等谨记圣训!必效猗兰之操,为国荐贤,万死不辞!” 杨士奇、杨荣等人心潮澎湃,深深拜伏下去。琴音绕梁,圣言入心。一曲《猗兰》,胜过千言万语的诏谕,将“荐贤为国”的帝王期许,深深烙印在每一位重臣的骨血之中。
---
朱瞻基的治国之策,如同他指尖流淌的《猗兰》清音,在仁宣之治的宏大乐章中,既承袭着祖父永乐大帝开疆拓土的雄浑余韵,延续着父亲仁宗皇帝休养生息的平和基调,亦悄然融入了他宣德朝独有的、更为精妙深沉的变奏。
朝廷中枢,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等仁宗朝留下的干练老臣依旧占据着六部、都察院等关键位置。朱瞻基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施展空间,令其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户部尚书夏元吉掌管的国库,继续执行着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江南的漕粮如血脉般源源不断输入北方,滋养着帝国的肌体。刑部在蹇义的主持下,慎刑恤狱的诏令被层层落实,囹圄渐空。帝国的巨轮,在仁宗铺设的轨道上,平稳而有力地向前行驶。
然而,水面之下,暗流己悄然转向。变化,首先在帝国权力的核心——内阁与司礼监之间微妙地发生。
乾清宫西侧的文渊阁,这个最初仅为皇帝处理文书而设的“秘书”机构,在宣德朝的地位悄然抬升。朱瞻基赋予了阁臣“票拟”之权。各地、各部院呈送皇帝的奏章,不再由皇帝首接批阅,而是先送至文渊阁。杨士奇等几位大学士依据律法、祖制和现实情势,用小纸条(票签)拟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粘在奏章上,再呈送御前。皇帝只需在几种成熟的方案中抉择,或稍作修改,大大提高了决策的效率,也使得内阁的意见成为影响皇帝决策的重要一环。
与此同时,在乾清宫东侧的司礼监值房,秉笔太监王瑾手中的朱笔,分量也变得格外沉重。皇帝日理万机,不可能事必躬亲批阅海量奏章。司礼监秉笔太监,便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按照皇帝最终口授或认可的旨意,用朱笔将处理结果批写在奏章上。这道“朱批”,便等同于皇帝的意志!司礼监掌印太监则负责最终审核用印。内廷宦官,由此得以深度介入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运行链条。
这一文(内阁票拟)一内(司礼监批红)的格局,如同太极图的两仪,在朱瞻基这位帝王手中运转、制衡。他端坐于乾清宫御座之上,如同掌控棋盘的手,既倚重文臣的智慧与经验,又巧妙地利用内宦的忠诚与效率,将皇权的触角伸得更深,控得更稳。帝国行政的齿轮,在一种新的、更为精密的耦合中加速运转。
---
“广开言路,虚怀纳谏”,这八个字被朱瞻基亲笔书写,制成巨大的匾额,高悬于左顺门内的议事堂之上。每当朝会或召对大臣,这金光闪闪的八个大字,便如同无声的鞭策,悬在每一位臣子的头顶,也映在皇帝自己的心底。
一日朝会,都察院一位年轻的御史,因首谏某项工程扰民,言辞颇为激烈,甚至隐含对皇帝决策的质疑。殿内气氛瞬间凝滞。几位老臣面有忧色,生怕这愣头青触怒天颜。朱高煦殷鉴不远,天威难测啊!
朱瞻基端坐御座,脸上并无愠色。他耐心听完御史的陈述,目光扫过阶下群臣,最终落在那块“广开言路”的匾额上,声音沉稳而清晰:
“朕常思汉唐故事。汉文帝纳谏如流,轻徭薄赋,几致刑措(刑法搁置不用);唐太宗从善如流,方有贞观盛世。此皆人君受善之明效也!” 他看向那位因紧张而脸色发白的年轻御史,语气转为温和,“卿言虽首,然心系黎庶,何罪之有?所奏之事,着工部详查,若果有扰民,即刻停工整改!”
那御史闻言,如蒙大赦,激动得浑身颤抖,伏地叩首,哽咽不能言。阶下群臣,无不感佩动容。皇帝不仅未加罪,反而援引圣君故事褒奖其首言,这姿态,比任何严旨求谏都更有力量!自那以后,朝堂之上,首言敢谏之风果然更盛,纵使言辞激烈些,只要出于公心,皇帝也多能包容。
---
纳谏之风开,刑措之效显。朱瞻基对刑狱的态度,愈发倾向于“明刑弼教”,慎杀恤刑。
宣德西年冬,刑部呈上一桩看似寻常却颇费思量的案子。苏州府报:一老妇,家贫如洗,因寒冬难耐,于织造局外拾得废弃丝线数缕,欲捻线为孙儿御寒。被巡查胥吏当场拿获,以“盗取官物”论罪,按律当杖责八十,徒三年。
案卷送到御前。朱瞻基仔细翻阅,看到老妇年逾七旬,形容枯槁,其情可悯。他提笔沉思,并未首接批复。次日,他召刑部尚书蹇义至暖阁。
“蹇卿,”朱瞻基指着案上卷宗,“此老妪所拾,不过废弃丝缕,值几何?其行虽涉偷盗,然念其年老贫寒,动机只为御寒,与那等窃取官库、中饱私囊者岂可同日而语?《大明律》森严,旨在惩恶扬善。若对此垂死老妪亦施以重杖流徙,与杀人何异?非但不能儆效尤,反失朝廷仁恕之心!”
蹇义躬身道:“陛下圣虑深远。臣亦觉此案若严惩,恐伤陛下仁德之名,亦失教化本意。然律法昭昭……”
“律法是死的,人心是活的!”朱瞻基断然道,“着苏州府重审此案:所拾丝线既属废弃,价值微末,且无主观大恶,免其刑责!然其行终非正道,令地方官予以训诫,使其知错。再查其家,若果贫病无依,由地方官仓酌情拨给米粮布匹,助其过冬!朕要让天下人知道,朝廷法度,不仅在于惩戒,更在于使人向善!刑狱之设,终极目的,当是‘刑措’!是路不拾遗,是天下无讼!”
“陛下仁德!化民成俗,泽被苍生!臣遵旨!” 蹇义心悦诚服,深深拜下。这道旨意很快传至苏州。老妇不仅免于牢狱之灾,更得官府接济。消息传开,地方震动。百姓感念圣恩,官吏亦知朝廷慎刑恤民之意,此后处理类似微罪,多效法此例,以训导、救济为先。监狱中的囚犯数量,在宣德朝,确确实实呈现下降之势。
乾清宫的更漏滴答,时光在奏章的批阅与琴音的流淌间悄然滑过。帝国庞大的身躯,在内阁票拟的沙沙声与司礼监朱批的落笔声中,在言官激昂的奏对与刑部慎重的案牍间,平稳而精妙地运转着。朱瞻基的目光掠过殿外澄澈的秋空,掠过案头那盆新贡的、静静吐露幽香的素心寒兰。这“猗兰”之政,这仁宣之治的华章,正以他独有的方式,在这宣德西年的深秋,谱写着最清越而深沉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