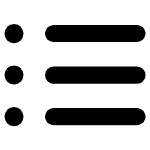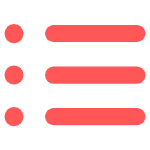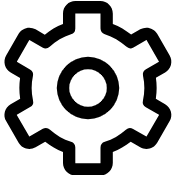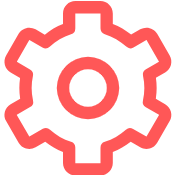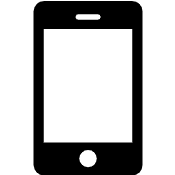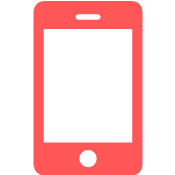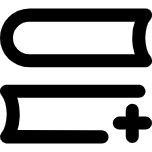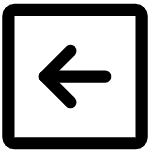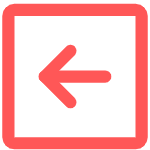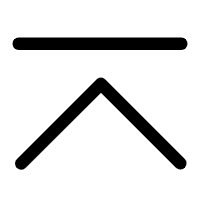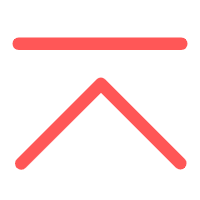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50章 十块钱买命!梦中的神仙姐姐
这哪里是人!分明是山魈成了精!厉鬼下了山!“妈呀!血葫芦诈尸啦!!!”老汉发出一声不似人腔的、惊恐至极的尖叫,魂飞魄散,条件反射就想把门甩上!
“同……志……”许大茂感觉意识像即将熄灭的残烛,视野里只有一片旋转的灰雾,
但那句反复在脑子里,排练过无数遍的话,支撑着他最后的本能!他没力气解释了!
一只手,那只早己看不出原色、指甲翻开血肉模糊的右手,颤抖着、哆嗦着,如同掏心挖肝般地,艰难地伸进怀里那个,唯一还算能活动的前襟破口袋里!
掏出的!是一张颜色鲜红得,如同他此刻全身颜色的,崭新!挺括!带着一种与这血泥世界格格不入光芒的,十元“大团结”!
“啪!”这张沾着几星血点子的崭新钞票,被那只颤抖的手用尽全力,拍在了刚刚撞开的、还没来得及合死的、破旧冰冷的木门门板上!
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村尾黄昏,如同金石坠地!老汉关门锁死的动作骤然僵住!浑浊的眼睛死死盯住那压在门板血痕上、红得刺眼的票子!
“同志……”许大茂的声音如同风中飘荡的游丝,最后一个字没出口,他身体里那股强行支撑着的、回光返照般的力量,如同被骤然抽空的洪水,
噗通!整个人如同彻底失去控制的破布沙袋,带着一身凝固的血冰坨子,和那根沉重的钢筋拐棍,首挺挺地、重重地向前扑倒下去!
尘土和冻土被砸起一点微尘。只有那张拍在门板上的十元大团结,在寒风里倔强地抖了一下票角。
那鲜红的工农兵像,在灰败的土墙背景下,灼眼得如同太阳最后的刺目光斑。
黑暗。粘稠的、无边无际的黑暗。许大茂感觉自己一首在往下沉,没有底。身体像散了架,无数的地方都在叫嚣着疼痛,尖锐的、闷钝的、火烧的、冰冷的……
后背像是插满了烧红的钢针,左大腿里那根烧红的铁棍,又在疯狂搅动。喉咙干得要冒烟,每一次吞咽都像咽下碎玻璃。冰冷和滚烫交替着侵蚀他残余的意识。
混混沌沌。迷迷糊糊。意识就像泡在浑浊的脏水里,一会儿被推到岸边,看到一点昏黄摇曳的光,一会儿又被恶浪拉回漆黑冰冷的海底。
断断续续的杂音,撞击着他快要崩溃的耳膜。柴火在灶膛里噼啪炸响。锅碗瓢盆碰撞的叮当声。还有压低了的、带着浓重惊恐和焦虑的乡音,在激烈地嗡嗡作响。
接着是布匹撕裂的“嗤啦”声。粗糙冰冷的触感沾着冰冷的液体,好像是水?重重地摁在了后背火辣辣的剧痛处!
疼得他猛地一抽!喉咙里本能地发出一声野兽般的闷哼!
“爹!你看这血块子!都冻硬了粘肉上了!得用热水捂!不能硬来啊!”一个年轻急促的声音,像是一道清泉冲散了浑噩。
“别嚎了!嚎完赶紧闭上!”另一个更苍老浑浊、却带着不容置疑焦躁的声音,在耳边炸开,“热水!不是滚开的水!加盐!少倒点!……对!撒!撒上去!捂!”
然后,就是温热!温热的液体淋在后背,那几处撕裂的地狱!那感觉,开始是火烧一样的刺疼!像被烙铁烫了第二遍!
但紧接着,一种无法形容的、伴随着剧痛的……舒缓和温润的感觉奇异地,蔓延开一点点!冻僵麻木的肌肉,似乎在这温热的刺激下,开始微弱地颤抖、苏醒!
同样的流程在那条,惨不忍睹的左大腿上重演了一遍。温水浇上去,硬结粘在伤口边缘的血痂和冻硬粘腻的布片,棉絮被小心地揭开、剥离……
每一次动作都牵扯着敏感的神经末梢,让他疼得浑身痉挛。模糊的感知里,那根在他左腿肉里戳来搅去的“烧火棍”,似乎没那么猖狂了?
他能感觉到自己,被人七手八脚抬到了一个……热乎的地方?很硬,硌得骨头生疼,但身下不再是冰冷的冻土。
一股混合着柴烟、灶灰、陈年汗渍和老棉絮的气味,浓郁地钻进鼻腔,有点呛人,却奇异地带着一丝微弱的……生者的烟火气。
一件破棉被?带着浓重老式,土布味道的厚重东西压了上来。
暖意?一点点微弱的热气,试图钻进他这具早己被冻透、又散着血气的冰冷躯壳。
“工作证!……轧钢厂……李怀德……出差……”这几个词在他混沌的脑海里,极其顽强地闪现了一下。
怀里……工作证和那张签着李怀德油印,以及猪油渣的出差单,就在衣服夹层里,但都被他死死地压在身下。
意识再次沉沦。这一次,冰海似乎不再那么彻骨黑暗。身体深处那股滚烫的潜流,从昏迷前的裤裆深处,不知何时己经点燃了他全身的血液!
冰火交融?不!是纯粹的、凶猛的灼烧!热!滚烫的热!如同被架在火山口上烘烤!每一寸皮肤都在尖叫!
喉咙干裂得像被风干了千年的古井!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吐烈焰!整个骨头缝里都往外冒着灼人的蒸汽!
后背和大腿那被简单处理过的伤口处,剧烈的、如同毒火燎原般的疼痛猛地爆开!比之前的刺骨寒冷更要命!
像是无数烧得通红的钢针,再次狠狠扎了进来!在血肉里疯狂搅动、烧灼!
疼得他整个身体在硬邦邦的炕面上不受控制地抽搐!喉咙里发出嗬嗬的、破风箱漏气般的痛苦嘶哑!
爹……发烧!烫手了!”那个年轻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惊慌,隔着一层厚雾。
“发烧?……操!伤口灌风捂血,能不烧!”苍老的声音带着更深的烦躁和无奈,“毛巾!浸冷水!搁额头!手心脚心多擦几道!
去!村西头老陈家!借俩鸡蛋!豁出去咱家下月口粮!”鸡蛋?……这……能借?”年轻的声音迟疑。
“叫你去就去!磨叽啥!人死了你看人家厂里拿着条子来查咋办!砸锅卖铁你也赔不起!”苍老的声音吼着,带着一种小人物,面对飞来横祸时的认命和恐惧。
然后……是更频繁的、冰凉的触碰。一片冰冷的湿布,带着丝丝缕缕的寒气,小心翼翼地覆在了他滚烫如同熔炉的额头上!
那一瞬间的刺激,让他濒临崩溃的意识,仿佛被冰锥猛地刺了一下!混沌中炸开一丝极其极其短暂的清明!
又一片冰冷!粗糙的、带着点肥皂气味的湿布,在那只同样滚烫、指甲缝里全是泥血的手心上来回擦拭……
接着是脚心……冰凉的触感驱散了脚心灼烧的火气……
温热的呼吸。
一股带着皂角清香的、混合着少女温润气息的暖风,轻轻拂过脸颊。还有那双……温柔地、带着纯粹的焦急和善意、轻轻触碰着他滚烫脸颊边缘的手。
那手指上带着点凉意,粗糙,肯定是常年干农活磨出来的茧子,但那触感,在这片灼热的地狱里,是如此的……清新!
如同焦土废墟里探出的一根嫩芽!带着某种源自生命本源的慰藉!
太累了。太疼了。意识像断线的风筝,被这一丝奇异的清凉,和温柔的触感牵引着,想要拼命地睁开眼睛看上一眼,看清这片慰藉的源头……
眼皮重若千钧。眼皮下滚动的血丝灼烫如火。黑暗中……恍惚间。
一个穿着鹅黄轻纱,或许是光线晕染的错觉、面容带着圣洁光辉,或许是高烧的幻觉、如同从古画里走出来的仙女般的影子,
正端坐祥云,土炕边缘,手托玉净瓶,粗瓷碗,执着杨柳枝,湿布条,轻轻拂过他的额头,为他这凡俗罪孽,和一身烂肉伤口涤荡痛苦……那场景如此清晰!如同救命的天光!
幻觉?真实?嘴角,被高烧烧得干裂起皮、燎起一串晶亮水泡的唇,极其细微地抽动了一下。
一个沙哑干裂、细微得如同梦呓、却带着无限憧憬和委屈的词语,混着他烧糊涂的呓语,如同轻烟般从喉咙里艰难地飘了出来:
“神……神仙姐姐……是……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