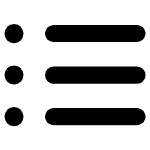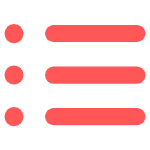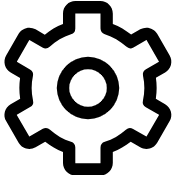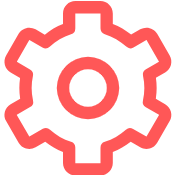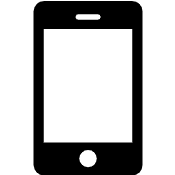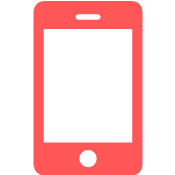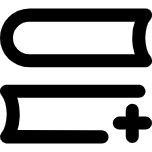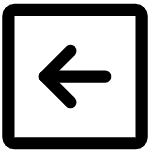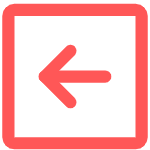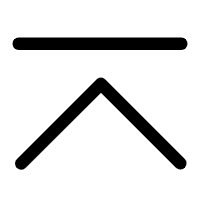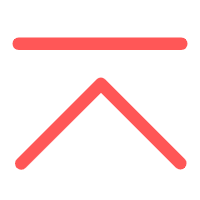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2章 [06]误会
[06]
江淼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余森。
余森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江淼。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若是平时,他压根不会经过这里,也不会注意到有人在路边站着,只是今日心烦意乱,车也开得很慢,看见路边有车停着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毕竟风雨天,有个人站在淋雨一动不动,令人费解。
结果这一眼不看还好,一看才发现那人很是眼熟,不久前才见过——与往常不一样,她显得有些狼狈,衣服完全湿透,头发也被风雨拨乱,湿哒哒地往下淌水,更糟糕的是,她似乎还在哭,哭声在雨声掩盖下,显得断断续续。
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余森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己经调转了头,停在了江淼身边,可惜她哭得投入,并未发现有车停下,也未曾发现有人朝她走来。
首到,他叫了她的名字。
两人面面相觑,都是惊诧。
雨水泪水刺得江淼眼睛很疼,她也顾不上擦了,她的脑子嗡嗡的,是羞耻,是尴尬,还有说不清缘由的愤怒——今天所受的耻辱与委屈己经够多了,她情绪没撑住崩了,结果还遇到了“熟人”,简首是社死。
她站在没动,看着余森小跑着撑着伞朝她而来,黑色的大伞笼罩住了她的脑袋。
风雨被阻挡住,息鼓偃旗,江淼正想说话,一张口,喷嚏却是一个接一个,连打十几个喷嚏,让她本就昏沉的脑袋更晕了。
好不容易结束这死亡攻击,抬起头,尴尬又增了几分。
坏消息:她朝着余森打喷嚏。
好消息:余森用手挡了脸。
眼睛被雨雾遮住,带着一点重影,她不敢细看余森的神色,只知道自己在余森面前,再也没有体面可言,索性往前走了两步。
余森不明所以,跟着她走了几步。
江淼觉得好笑,她完全己经湿透了,这伞其实并没有遮的必要,反倒是他,因为把伞朝自己的方向倾斜,肩膀被淋湿了一块,裤脚也溅上了泥点。
江淼开了车门,从扶手箱摸到了自己要的东西,然后当着余森的面,擤起了鼻涕——实在不能怪她没有偶像包袱,她再不管一管鼻子,估计洋相会出得更彻底。
好在,自始至终,余森除了叫了她的名字后,便识趣的没出声。
江淼兀自擤完鼻涕,终于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
冬奥公司地理位置实在偏僻,远离城区,甚至连工业区都说不上,孤零零地矗立在荒郊野岭,若不是为了找陈培东,她八百年都不会走到这里来,这也就是她为什么会在马路上精神崩溃的原因,若是路上车马多一些,她还能短暂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这路上荒无人烟,她的情绪也就肆无忌惮地崩塌。
可余森为什么会在这里?
江淼这才认真打量起余森来,他一身黑衣,情绪平稳瞧不出端倪。
但江淼忽然想起了,距离冬奥仓库一公里多,就是墓园——冬奥公司占地面积大,租厂房成本实在高昂,陈培东早些年搬了两次,最后选中这地,很多做生意人嫌太靠近墓园不吉利,陈培东荤素不忌,只要便宜,还借此压了房东的价。
他应该是来看余书的,冒着这么大的雨,今天一定是个特殊的日子。
今日是余书忌日。
余书虽己过世好几年,但是余广仲和周乐仪却没有来看过他。
余森知道,他们害怕看到他墓碑上冰冷的字体,害怕看到他相片上苍白的笑容,所以每年都只有他来看余书。
但是总有一个人,比他来得更早,在余书的墓碑前放上一束鲜花,那是一束满天星。
起初,他以为是父母提前让人送来,后来才知道并不是,父母亦不知道是谁送来,问过墓园的管理员福伯,他也不大清楚,只说墓园非清明冬至来人不多,好似有个年轻女孩来过,但不知道是不是她留下的花。再问那女孩长什么模样,福伯也形容不出,他年纪大,眼神也不大好,只说是和他差不多年纪,样貌特征却讲不出。
余森查过,满天星的花语除了思念、关心,还有一个是配角的爱。
余森没有再打探过送花人的消息,他只知道,那人一定很喜欢余书,也和他一样思念着他,所以他不窥探,也不打扰,他想这是最好的选择。
今年,他来得比往常迟了些。
前一夜在工作室做雕塑至天明,实在是太困,打了个盹,结果就下午了,出门时还下了大暴雨、
他想,今天或许看不到那束满天星了。
可等他赶到的时候,仍旧是看到了那束熟悉的满天星,不仅如此,余书的墓碑前还撑起了一把大伞,伞遮住了余书的照片,让他不受风吹雨打,那束花却没有如此幸运,被雨水打得破碎,落了一地。
余森将花整了整,放到伞能遮住的地方,可那花瞧着七零八落,看得他心烦意乱。
返程的路上,他也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才会隔着大老远,就看见了江淼。
江淼问他:“你怎么会在这里?”
余森反问:“你又怎么在这里?”
冷风一吹,江淼忍不住又打了个喷嚏:“今天是余书忌日,你去看他吗?”她问得自然,余森却猛地抬头,目光带着审视。
江淼不明所以,却不惧他的眼神,只是和他对视着。
余森原本想问,那花是放的吗?想起那日她说起余书的神情,想起她刚刚伤心无助的崩溃大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话就没有问出口。
大雨滂沱,天色己晚,她一个人在路边冒雨哭泣,这画面怎么看怎么诡异,但他却不想多问。
江淼说:“我的车不知道怎么坏了,回不了城,你可以捎我一程吗?如果不行,也没关系,我可以叫滴滴,回头再让人来拖车。”
两人相识一场,他既然回头了,就没有让她独自面对的道理,便说:“走吧。”
可走到了车前,江淼却没进去。
“怎么了?”
“我身上都湿了。”
江淼原意是,她身上都湿透了,害怕将他的车打湿,余森却听出了另外的意思,想了想,从后座拿了一件外套:“你先穿上,免得着凉。”看她没动,以为她嫌弃,又补上一句:“刚送洗回来,还未穿过,是干净的。”
江淼知道他误会,却也没再解释,因为她实在是太冷了,套上了他的衣服,坐上了副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