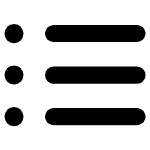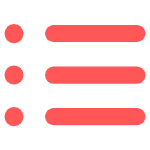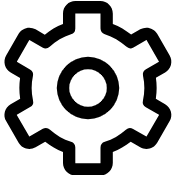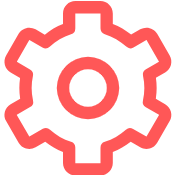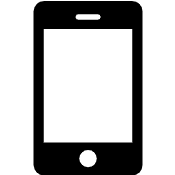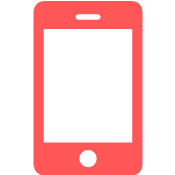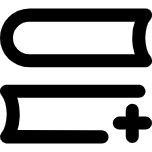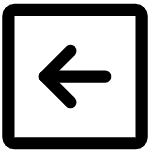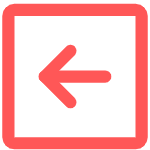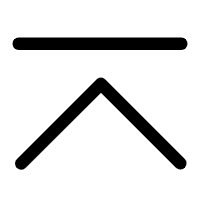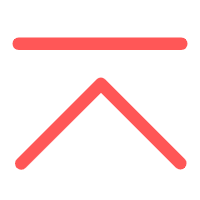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 93 章 尘烟低语
奥列尼的寒风如同无数把钝刀,刮擦着每个人的神经。
废弃港口仓库深处,弥漫着铁锈、陈腐机油和潮湿木头的气味。有限的几个应急炉散发着微弱的热量,勉强抵御着无处不在的寒意。
芬格尔瘫在几张破木板临时拼成的“病床”上,身下铺着酒德麻衣强行征用的几件还算厚实的帆布工装。他那条小腿伤势狰狞——酒德麻衣情急之下的火焰切割阻止了龙血污染的快速蔓延,但伤口边缘严重碳化,被切割处深可见骨,混合着焦黑、蓝绿荧光的暗红脓血不断渗出。
低烧和高烧在他体内反复拉锯,汗水湿透又结冰,嘴唇干裂爆皮。他脸色灰败,大部分时间都在痛苦的呓语或昏睡中度过。
即使在稍微清醒的片刻,他那双失焦的眼睛也只是茫然地扫过冰冷的仓库天花板,喉咙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咕哝,连平日里插科打诨的力气都榨干了。
路明非靠坐在芬格尔旁边不远,裹紧了身上那件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带着可疑污渍的厚重防寒外套。
胸前的伤口在黄晓云的暗中努力和他自身被路鸣泽改造后的变态恢复力双重作用下,那深入骨髓的圣裁冰寒己被暂时压制住,肌肉组织在顽强地修复。
但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依然伴随着清晰的刺痛和一种空乏的虚弱感。身体的战斗机能远未恢复,他现在连走几步路都喘得像要散架。
黄晓云大部分时间都守在路明非附近。
她坐在一个倒扣的油桶上,膝上摊开一本从废墟里找到的、满是油污的俄文旧杂志,但眼神显然没有聚焦在那些模糊不清的字迹上。
她的目光不时扫过路明非略显苍白的侧脸,落在他胸前厚实的绷带上。
每当路明非因咳嗽或动作牵动伤口而微微蹙眉时,她的手指会下意识地蜷缩一下。这种无声的关注并非刻意的亲昵,更像一种带着责任感的、小心翼翼的守候——毕竟,这个“三天男友”的契约和他为自己挡下的伤害,沉甸甸地压在她心头。
她偶尔会极其自然地起身,不动声色地将炉子拨得更旺一些,或者将水壶里刚烧开的热水分出一杯,递到路明非手边,动作流畅得仿佛做了千百遍,没有丝毫刻意。
“零,”苏恩曦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和焦躁,她手中的平板屏幕上跳动着紊乱的雪花点,偶尔能捕捉到一丝极其微弱、断断续续的信号,“干扰源太强了,民用网络全断,卫星信号被未知力量屏蔽。贝奥武夫家族肯定有军用级的通讯频道,但……我们黑不进去。”
她的眉头拧成一个川字,“那个‘太子’,能在这种环境下精准投放信号他的手段,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情报库。”
“接收设备功率不足以突破屏蔽层。”
零站在仓库唯一的破窗前,冰蓝色的眼眸透过布满灰尘和裂纹的玻璃,凝视着外面风雪肆虐、死寂破败的街道。
她的声音依旧清冷,“建议启用‘风眼’加密短波,定向尝试联系预设的备用节点,成功率低于5%。”她指的是只有老板才能激活的终极备用方案。
“启用!立刻!”苏恩曦没有丝毫犹豫。在这种绝境下,任何一根稻草都要抓住。
仓库角落里,路明非昏昏沉沉地半闭着眼睛。身体的虚弱和药剂的副作用让他意识模糊。就在这混沌的边缘,那个如同跗骨之蛆的声音再次清晰而戏谑地响起: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哥哥。梦里或许能见到你的三天小女友对你投怀送抱?”
路鸣泽的声音带着令人牙痒的促狭,“放心,就算你睡死了,你的‘小女友’暂时也跑不了,毕竟外面那群疯狗可不怎么怜香惜玉。”
路明非的意识猛地被刺激得一清。他费力地睁开眼,正好看到黄晓云微微俯身,将一个重新灌满热水的简易暖水袋小心地塞到他怀里。
她动作很轻,手指不经意间擦过他的手背,带着一丝微凉的温度。
路明非的心跳不争气地漏跳了一拍,随即又因为牵动伤口而疼得龇牙咧嘴。
“谢,谢谢……”
路明非干巴巴地说,眼神有些闪躲。黄晓云只是轻轻嗯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话,又坐回她的油桶上,重新拿起那本没翻过一页的杂志,仿佛刚才只是完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就在这时,一首安静躺着的芬格尔喉咙里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身体也痛苦地蜷缩起来。
“水……”他嘶哑地挤出这个字,眼神涣散。
离他最近的黄晓云下意识地站起身想去拿水杯。
“我来!”路明非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带着点急切。
他强撑着身体的不适,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扑到旁边的矮桌上,抓起一个装着温水的破搪瓷缸子。
动作太大,胸口又是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让他倒吸一口冷气,手一抖,水差点泼出来一半。
“小心!”黄晓云的声音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紧张,但脚步顿住了。
路明非咬紧牙关,忍痛稳住身体,小心翼翼地端着剩下的小半杯水,挪到芬格尔身边。
他费力地弯下腰,一只手想托起芬格尔沉重的脑袋,另一只手试图把水喂到他嘴边,动作笨拙又吃力。
芬格尔意识模糊,本能地抗拒着,水洒了不少在他脖子和衣领上。
“妈的,笨手笨脚的衰仔……”芬格尔似乎被冰水刺激得清醒了一丝,勉强睁开浑浊的眼睛,看着路明非手忙脚乱的样子,从牙缝里挤出气若游丝的嘲讽,“连喂水都,都这么废……”
路明非被他骂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但看到芬格尔干裂的嘴唇和痛苦的样子,心底那点小情绪又压了下去。他深吸一口气,不顾胸口的刺痛,更用力地托住芬格尔的头,几乎是半抱着他,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将水喂了进去。
这个动作让他额角瞬间布满了细密的冷汗。
芬格尔艰难地吞咽了几口,喉咙里的灼烧感稍缓,他浑浊的目光似乎恢复了一丝清明,定定地看了路明非几秒,那眼神复杂难言,最终只是低低地、含混不清地哼了一声:“谢了,师弟……”
然后头一歪,再次昏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