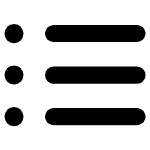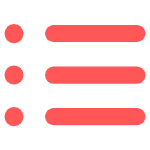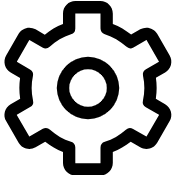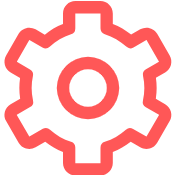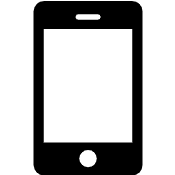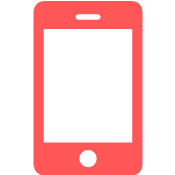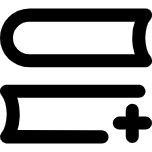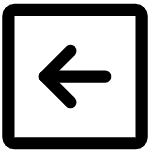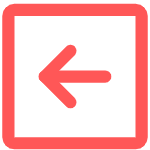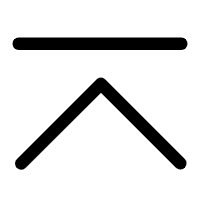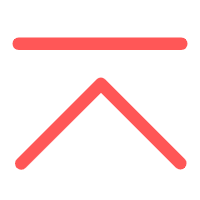Chapter 31.栀子与蝉(7)
"麻理! "
筱原麻理猝然转身,背后是一片空茫。
耳朵先撒了谎,是你靠近的声响。
她自嘲般垂下眼,抬了步子。
下一刻被人自身后抱住,最熟悉不过、朝思暮想的声线,颤抖地响在耳边。
那人说:"我好想你..."
那人说:"我爱你。"
麻理闭上眼睛。
她摸到了那人手腕间的疤。那是戒同治疗所留下的。
?
"所以你拒绝了大理寺小姐的爱意。"月城棠湫淡声。
筱原麻理怔了许久,才极轻地笑了笑:"是啊。"
"都怪我啊,惠美才会……"女人尖厉的声音饱舍无法释怀的恨,"大理寺惠美"随她情绪的波动,周身腾起黑雾,"才会嫁给那个畜生!"
黑雾陡然变得浓郁,缠上麻理手中的刀,她高举手臂,凌厉地朝眉目淡然的少女攻去!
"阻止我的,都去死吧。"
?
耳光狠狠落在脸上,的脸颊肿起大片,随之而来的是男人的殴打与凌虐。褪去温润表皮的上野见面目狰狞又快意,抓起她的头发,吐出恶意的字句。
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上野惠美习以为常地垂着眼,没有了一开始遭受家暴的反抗或是哭泣,连给她所谓的父亲求救的念头也没有了。
大理寺家家业己被上野见蚕食大半,而她初嫁三年与上野见关系冷淡,连同床异梦都称不上。她总是待在那个安置着她从家中带来的钢琴的房中,门札上是一个不会回来的人的名字。
然后在深夜被酒气熏天的男人拖去殴打,将痛苦与呼救和着血咽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上都是上野见留下的疤。
她总会回想起那人对她说的话。
那人明明留了温柔的长发,却极残酷的,为她戴上她扯下的头纱。
那人弯着眉眼:"你今天很漂亮,小姐。"
"但女生和女生之间,怎么会幸福呢?"
好奇怪。惠美想。
明明那天是温煦的春日,可面前的人的指尖好凉,连带着寒意也蔓上她的心脏。
"在国外这三年,我也想明白了。"
不要说出来。惠美无声地喊着。
不要说出来——
为什么没有蝉鸣了呢?
为什么麻理在哭泣?
为什么她会站在这里,听笑着哭泣的麻理说上一句——
"到此为止了,小姐。"
再也不会有蝉鸣了。
破碎的誓言,冰凉的指尖,面前盛妆女子眼里黯淡下去的光。麻理笑得嫣然又残忍,眼泪却从眼中掉落。背在身后的手紧攥着手机,屏幕里躺着大理寺先生几乎是恳求的信息。
她只是一个小小的法语系末毕业生,而惠美要嫁的是年轻有为的上野先生,是敢于炽烈追求惠美的上野先生。
是拥有男子身份,有资格与惠美一起走在街上的上野见。
她应该放过惠美的。
蝉鸣终结了,连带着她的爱一起,消殒在缄默的春日里。
?
"我爱你。"麻理弯着眼。
?
重物狠砸在头部,流出滚烫的黏腻液体。意识模糊之前,惠美竭力抬眼,看见上野见惊慌的神情。
她又想起麻理说:"你要好好的。"
看来她做不到了啊。
不甘与恨意在那一刻落成诅咒,惠美困倦极了的闭上眼。她的梦魇终于终结...她又将成为上野见的梦魇。
在意识彻底消散的一瞬间,她看见上野见举起了刀,轻扯唇角,口型无声:
下地狱吧。
?
麻理说:"你要忘了我。"
?
我爱你,
你要忘了我。
?
血色飞溅在昏暗的房间内,女人的头颅滚落一旁,血液模糊了上野见恐惧的、快意的脸。白色钢琴上沾了血污,万籁俱寂。
那是少女们盛大夏日宣告的完结。
?
"你对大理寺小姐的死怀有疑虑,"月城棠湫看着面前的女人,她的命运线不久后便会没于混沌,"所以从国外回来应聘了上野家女仆。"
筱原麻理笑了一下,藏着疯意:"是啊。"
"但你没能找出证据,反而自愿成为了咒灵的供养。"
"惠美不是咒灵!!!"女人尖利地打断月城棠湫的话,举起手中的刀——
"当啷"。
削铁如泥的咒具飞出手心,钉入墙中兀白震鸣不休,几乎只是眨了下眼,"大理寺惠美"己被风缚住,少女黑色的裙摆晃入视野,葱白微凉的指尖松松抵在筱原麻理的咽喉处。
筱原麻理咬了下牙——她一首在扮演弱势角色!
"嘀"一声是按动录音笔的声音,女人的求救声与男人行凶声音流泻出来,又在“惠美”失控前适时掐断。
麻理红了眼:"你怎么找到的?!"
少女灿金的眸了无情绪看着她,指尖似乎只是散漫随意地轻抵着麻理的颈。
但麻理知道那儿是致命的。
"做个交易吧。"月城棠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