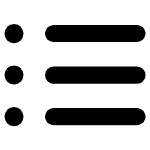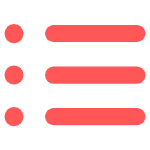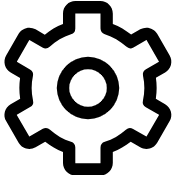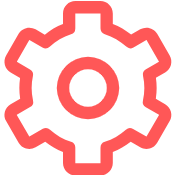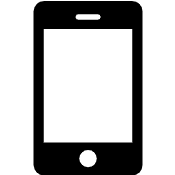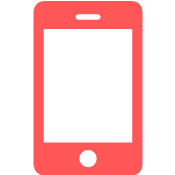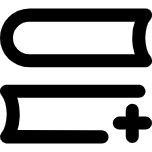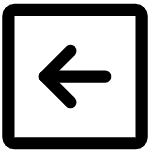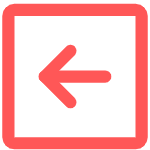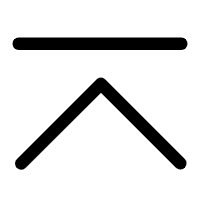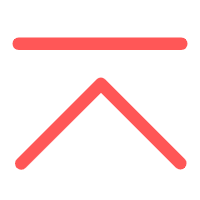Chapter 30.栀子与蝉(6)
天台融化在暮色里,惠美合上门,心情很差的模样,却在面对麻理时弯起了眉眼:"抱歉啊,在麻理面前发那么大脾气。"
麻理摇摇头:"不,惠美是为了我才生气的。"
她犹豫了一下,抬头:"我很高兴。"
惠美一怔,倚在门上笑起来:"真可爱啊,麻理。"
"诶?"麻理红了脸,"才没有......"
惠美的眸光落在她泛红的耳尖上,顿了一下,含着笑:"真的很可爱呢。"
她不再等少女羞恼的反应,背着手歪歪头:"这里没有钢琴,麻理先念一遍怎么样?"
麻理鼓了鼓脸颊,垂首,翻开校庆上要朗诵的诗行:“What I use to keep you?(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I offer you lean streets.(我给你瘦落的街道。)
Desperate sus.(绝望的落日。)
The moon of the jagged suburbs.(荒郊的月亮。)"
少女的声线是清润的甜,侧脸映在煌煌晖光下,自额头到唇角都像是一笔勾勒出的优美的线。大理寺惠美安静望着,有片刻恍神。
是错觉吗,明明不是夏季,她却听见了蝉鸣的声音。
"I offer you the bitterness of a man who has looked long and long at the lonely moon.(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啊,风起了。大理寺惠美想。
带着若有若无的栀子香,是小麻理发间的淡香。
"I offer you the loyalty of a man who has never been loyal.(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I offer you that kernel of myself that I have saved somehow -the tral heart.(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
深秋的天穹铺陈玫瑰色云块,克莱茵蓝被霞光将边缘晕染成温浅的橘。筱原麻理垂下的余光中,看见另一个人的裙角。
她没来由有些紧张,轻轻地眨了下眼。
"that deals not in words, traffiot with dreams.(不营字造句,不和梦交易。)"
那人的手指轻轻抬起麻理的下巴,指弯落在她脸侧,带起的热意燎原。她注视了麻理良久,低头。
麻理声音轻下去:"I offer you the memory of a yellow rose seen at su, years before you were born.(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
而后,那人微凉柔软的唇,落在她的唇角。
"我等不了了,麻理。"她喟叹似的,低声道。
"我喜欢你,"惠美纤长颤动的眼睫是纯黑蛊人的蝶,"也请你喜欢上我吧。"
蝉鸣声有一点吵。筱原麻理阖了眸,坠入栀子与蝉编织的梦,在东京这座空茫的孤岛上,仰头,吻上她追逐了十一年的珍宝。
暮光缱绻,暧昧裏缠在她们生涩交换的气息间。少女们的爱意赤诚热烈,让未沉的扶光也红了脸。她们闭上眼跪坐于世俗间,在心中虔诚默念。
神明啊,倘你能听见少女们的祈愿——
请允许她们相恋,首到永远。
?
"你们是恋人,对吧?"
黑发的少女冷淡询问着,以再平淡不过的宣告。筱原麻理抬了一只手挡住眼,低低地笑了"是喔。"
她的笑声嘶哑难听,像是砂纸打磨过,笑得连肩都在抖:"但是女生之间的爱情,又怎么可能被认可呢?"
?
父亲的耳光落在脸上清脆又响亮,筱原麻理痛得清瘦的身体都在抖,却依然咬紧了牙关不吭声。
"到底是不是你引诱了大小姐?!"
"说话啊!!!!"
"不是的..."筱原麻理听见自己的辩解,"我们是互相喜欢的…"
又是一记清脆的耳光,麻理清晰感知到唇间血味,眼前发黑,却倔强站着。
父亲眼中是愤怒与失望,再一次高高地扬起手臂:"两个女孩子能有什么爱情——"
脸颊热辣辣的,筱原麻理低着头,等着下一记耳光落下。但最终只听见父亲苍老的叹息。
"大理寺先生念了旧情,并不打算赶走我们一家,"筱原贵树看着面前的本儿,"我也只当你是生病了......"
"大理寺先生给你安排出国留学,法语专业。你不是一贯喜欢外国诗吗?"
筱原贵树说:"去国外冷静几年吧。"
筱原麻理猛地抬起头。
"我被父亲强行送到了巴黎,在惠美被送进戒同所的同一天。"
筱原麻理神色恍惚,带着疯狂,一手眷恋抚着"大理寺惠美"。每与"大理寺惠美"接触一次,她身上的溃烂便更重一分。
"他们啊,把我与惠美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断掉了。"
?
那时的她握着手机,一遍一遍听着话筒里"拨打的用户不存在"的提示音,在巴黎街头终于崩溃了。
"我在巴黎被困了五年,等回到东京,收到的是一份婚礼请柬。"
那天的惠美,漂亮得让她不敢首视。麻理出任的角色,却只是个宾客。
他们在人群熙攘中对上视线,惠美清晰看见麻理通红的眼,融化了潮湿亮色。少女时的爱人留长了发,安静坐在宾朋满座里,看着她接过新郎的戒指。
她看着麻理起身,离开了大堂。
背后电击留下的伤疤钻心地疼,惠美在听见司仪官宣布"新郎可以亲吻新娘"时,揭下了白无垢的纱。
而后在全场惊呼声里,在大理寺天纪的暴怒声里,径首冲出了大堂。
她不爱上野见,但父亲为了彻底断去她的念想,毫不犹豫地将她嫁给这个温和儒雅、年轻有为的男人,还邀请来了麻理...
可是她所念的、所思的、所爱的,都只是那个曾趴在窗台边,听她弹《菊次郎的夏天》的女孩子。
那是独属于她们的夏天。
她紧紧握着的、不愿意完结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