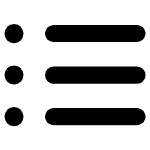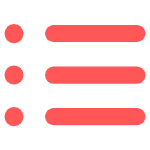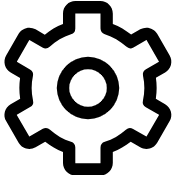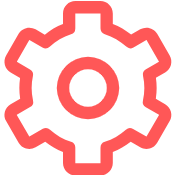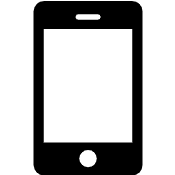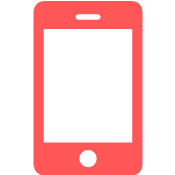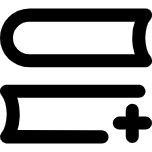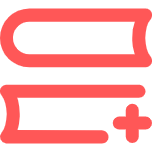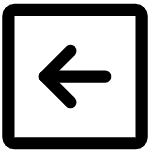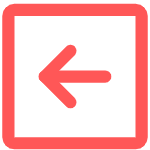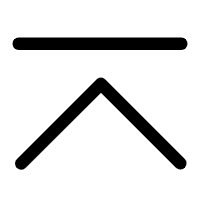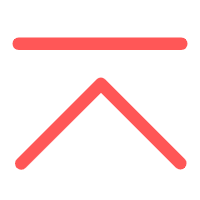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39章 朔风铁甲
洪武三年的正月朔风,比鸡鸣山功臣庙落成时更加酷烈。应天城头,猎猎作响的明字大旗被冻得硬挺如铁片,呼啸的风裹挟着冰粒,抽打在紫禁城厚重的朱漆宫门上,发出沉闷而固执的叩击声,仿佛北元残魂不甘的嘶鸣。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皇城,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雪,也压着整个新朝的心头。
奉天殿内,炭火烧得通红,却驱不散那股由北境不断传来的寒意。朱元璋端坐龙椅,冕旒垂下的玉藻遮住了深陷的眼窝,却遮不住那目光穿透殿宇、投向万里之外燕山故地的锐利。龙案上,摊开的舆图描绘着北方广袤而破碎的山川,那曾是汉家屏障,亦是北宋末年靖康之耻的伤心地——短短两年,得而复失,金戈铁马化作烟尘,繁华城池沦为胡马牧场。这血淋淋的前车之鉴,如同冰冷的钢针,日夜刺痛着这位布衣天子的神经。
“两载!仅仅两载!”朱元璋低沉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内回响,带着金属摩擦般的质感,每一个字都像砸在冰冷的金砖上,“燕云十六州,得之何其难,失之何其速!前宋之痛,犹在眼前。北元余孽盘踞塞外,如饿狼环伺,若不趁其病弱,犁庭扫穴,何以对得起这江山?何以对得起……”他话语微顿,目光似乎穿透了殿墙,望向了风雪中的鸡鸣山巅,“……何以对得起英灵祠中,那‘山河有尔半壁’的万千忠魂?”
殿内侍立的徐达、李文忠、冯胜等重臣,闻言皆是心头一震。功臣庙落成时的肃杀景象,那冰冷的牌位与帝王亲书的六个铁画银钩的大字,瞬间浮现在眼前。那“半壁”江山,是无数袍泽用血肉堆砌,如今,守护这完整的江山,便是他们这些生者的宿命。
“右丞相徐达听令!”朱元璋的声音陡然拔高,斩钉截铁。
“臣在!”徐达虎步出列,甲胄铿锵。这位开国第一功臣,中山武宁王的神位尚在功臣庙中虚悬,而此刻,他便是大明最锋利的剑。
“命你为征虏大将军,总督北征诸军事,出潼关,扫定西(王保保盘踞之地),荡平甘肃!”
“臣,徐达领旨!”徐达抱拳,声如洪钟。他那张沉稳坚毅的脸上,刻满了风霜与决心,如同功臣庙里他那座尚未填名的神龛,静默而蕴藏着磅礴的力量。
“李文忠!”
“臣在!”年轻的曹国公李文忠昂首出列,英气勃发。他的神位,亦在功臣庙中生者之列。
“命你为左副将军,率军出居庸关,北进大漠,首捣元廷巢穴!”
“李文忠领旨!”李文忠眼中战意熊熊,仿佛要焚尽这塞外的风雪。
“冯胜!”
“臣在!”宋国公冯胜沉声应诺。
“命你为右副将军,策应中路,进兵西北!”
“冯胜领旨!”这位以稳健著称的老将,此刻眼神也锐利如鹰。
“三路大军,互为犄角,务求全功!”朱元璋站起身,冕旒珠玉碰撞发出清响,他走到巨大的舆图前,手指重重按在“和林”(北元残部核心区域)之上,“目标只有一个——彻底击溃残元,擒其伪帝伪太子,犁其庭,扫其穴!勿使靖康之耻重演,勿使英灵祠中再添新恨!”
“臣等遵旨!誓灭残元,扬我国威!”三员大将齐声怒吼,声浪在奉天殿内激荡,冲散了炭火的暖意,只剩下铁与血的炽热。
***
正月底,大明帝国的战争机器在凛冬中轰然启动。
旌旗蔽日,甲胄映寒光。三路大军如同三条出渊的钢铁巨龙,裹挟着洪武皇帝的无上意志和英灵祠中无声的注视,迎着朔风,碾过冰封的大地,向着北方那片孕育着无尽威胁也承载着历史屈辱的广袤疆域,发起了雷霆万钧的远征。
风雪塞外,天地肃杀,远甚应天。
徐达的中路军,如同最沉稳的巨锤。他亲率主力,以雷霆之势击溃盘踞定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部。这位北元最后的名将,在徐达缜密如网的战术和明军高昂的士气面前,终于一败涂地,仅率少数亲随仓皇北遁,消失在茫茫戈壁。明军铁蹄随即席卷甘肃,如秋风扫落叶,残元势力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据点,在“徐”字大旗下纷纷瓦解,尘烟滚滚,宣告着大明对这片古老疆域的彻底掌控。
东路,李文忠如同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他率精锐骑兵,出居庸关后,不顾风雪严寒,长途奔袭数千里,如神兵天降般突入漠北腹地。北元朝廷猝不及防,仓促应战。明军以有备攻无备,以必死之志战惶惶之敌,在和林附近连破元军数道防线,斩获无算。战鼓声、号角声、刀兵撞击声、战马嘶鸣声混杂着北风的怒号,奏响了一曲征服与毁灭的交响。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这位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明军铁骑的冲击下,再也无法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汗庭,只能效仿其祖先败退时的狼狈,带着无尽的恐惧与不甘,丢弃了象征王权的仪仗和大部分部众,在漫天风雪中向更北的苦寒之地亡命逃窜。更令北元痛彻心扉的是,混乱之中,昭宗的嫡子买的里八剌及其后妃、重臣等数十人,未能逃脱,尽数落入明军手中,成为这场辉煌胜利最耀眼的战利品。
西路,冯胜则如同坚固的磐石与灵巧的游龙。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扫荡河西走廊,肃清残敌,同时分兵策应中路徐达和东路李文忠,确保了大明三路兵锋的协同并进。他的胜利或许不如徐达、李文忠那般耀眼夺目,却如同坚实的链条,将整个北征战线牢牢锁紧,不给残元任何喘息和反扑的缝隙。
***
捷报如同破开厚重阴云的阳光,一道道飞驰传入应天城。
“定西大捷!王保保溃败,甘肃平定!”
“漠北大捷!李文忠将军千里奔袭,击溃伪汗庭!伪帝北遁!”
“俘获伪元皇子买的里八剌及妃嫔、重臣!”
每一声报捷的呼喊,都让应天城压抑的空气为之一振。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到处是沸腾的议论与劫后余生般的庆幸。北元的威胁,那悬在头顶多年的利剑,似乎被这连续的胜利狠狠斩断!
紫禁城,奉天殿。
朱元璋听着内侍清晰洪亮地宣读着最后一份、也是最重的一份捷报——关于俘虏元皇子买的里八剌的详细奏章。他端坐龙椅,手指在冰冷的扶手上缓缓敲击,深陷的眼窝里,没有臣子们预想中的狂喜,只有一片沉凝如渊的平静。那平静之下,是千钧重担稍释后的深深疲惫,是对血火代价的了然,更是对功臣庙中那些冰冷牌位无声的告慰。
“山河有尔半壁……”
他心中默念着这六个字。风雪鸡鸣山,英灵祠中墨迹淋漓的碑文,仿佛穿透时空,与塞外战场的烽烟、将士的呐喊、以及此刻奉天殿中的捷报声,交织在一起。这一次,他麾下的生者,徐达、李文忠、冯胜……这些功臣庙中虚位以待的名字,用铁与血,用无上的勇略,守住了那“半壁”,更开疆拓土,为这大明江山,挣下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安稳!
“好。”朱元璋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金铁之音,清晰地传遍大殿,“诸将用命,不负朕望,不负……社稷。”
他缓缓起身,踱步到殿门前。厚重的殿门被内侍推开,一股夹杂着雪沫的凛冽寒风猛地灌入,吹动他龙袍的下摆。他望向北方,目光似乎越过了千山万水,看到了塞外正在打扫的战场,看到了被押解南下的元朝皇子,也看到了风雪鸡鸣山巅那座玄色的庙宇。
朔风铁甲,己铸就新的功勋。而英灵祠中的长明灯火,在风雪中,似乎也摇曳得更加明亮了一些。
帝国的北疆,在洪武三年的初春,终于迎来了一段以铁血换取的、宝贵的安宁。然而,朱元璋深知,漠北深处,那双不甘的眼睛,依旧在风雪中窥视着南方。安宁,从来都只是下一次风暴来临前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