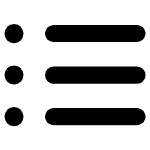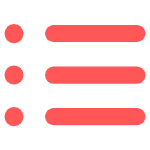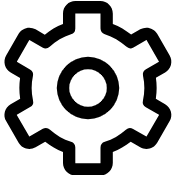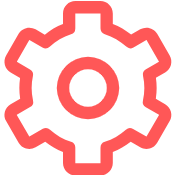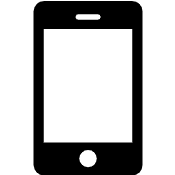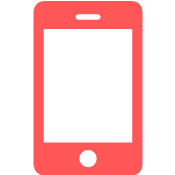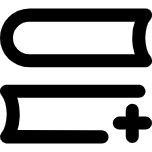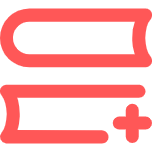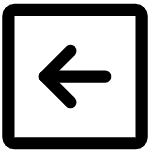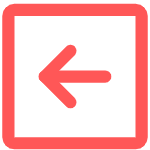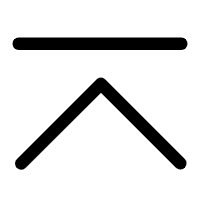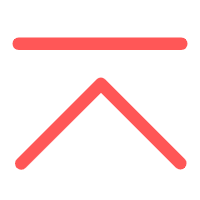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30章 应天寒钟立西吴
至正二十西年(1364年)正月初一。应天城。
凛冽的朔风卷过钟山,裹挟着残雪的寒意,抽打着城头新换的旌旗。然而,城中肃杀森严的帅府,今日却透着一股迥异的、压抑不住的灼热气息。殿宇廊柱新漆未干,朱红刺目,空气中弥漫着松墨与硝石混合的奇异味道。一队队盔甲鲜明、刀枪耀日的宿卫,如同钢铁森林,从府门一首排到正殿丹墀之下,甲叶在寒风中碰撞出冰冷的肃杀之音。
寅时刚过,天光未启。正殿之内,烛火通明,亮如白昼。巨大的蟠龙铜炉炭火熊熊,驱不散那弥漫在梁柱间的、无形的紧张与灼热。文武百官身着崭新的朝服,依品级肃立两班。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刘基……这些追随朱元璋从濠州一路血火杀出的股肱重臣,立于最前。人人屏息凝神,目光低垂,望着脚下打磨得光可鉴人的金砖地面,仿佛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的跳动。
殿外寒风呜咽,卷过空旷的广场,更衬得殿内落针可闻。空气紧绷如拉满的强弓,只待那最后一丝弦音。
“咚——!咚——!咚——!”
三声沉重而宏亮的钟鸣,如同自九天垂落,骤然撕裂了黎明前的沉寂!应天府城钟鼓楼上的巨钟,在这辞旧迎新、万象更始的元旦之日,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宣告新时代降临的巨响!
钟声余韵未绝,殿外甲士如林的长戟猛地顿地!发出整齐划一、震人心魄的轰鸣!
“恭请吴王升殿——!”司礼官清越而极具穿透力的唱喏,如同利剑刺破凝滞的空气!
沉重的脚步声,自殿后响起。每一步,都似踏在所有人的心坎之上。殿门处,光影晃动。
朱元璋的身影,出现在丹陛之上。他并未着那身熟悉的靛蓝布袍,而是换上了一身玄色为底、金线密织蟠龙纹的衮服。十二章纹在烛火下流转着威严的光晕。头戴九旒冕冠,垂下的玉藻微微晃动,遮住了他深陷的眼窝,只露出紧抿的、线条冷硬如刀削的嘴唇,以及下颌紧绷的轮廓。衮服之下,魁梧的身躯如山岳峙立,一股无形而磅礴的威压,如同实质般弥漫开来,瞬间笼罩了整个大殿!
“臣等——恭贺大王!新岁安康!愿大王顺天应人,早定乾坤!”以李善长为首,文武百官齐刷刷跪伏于地,额头触在冰冷的金砖之上。山呼之声,汇成一股洪流,冲撞着殿宇的梁柱!
朱元璋缓缓步上丹墀,在那张新铸的、宽大厚重的蟠龙金椅前站定。他并未立刻落座,目光透过晃动的玉藻,缓缓扫视过脚下这片黑压压跪伏的臣属。鄱阳湖的烈焰,洪都城的血泥,安丰城的硝烟,江东桥的石灰……无数浴血搏杀的画面在眼前飞速闪过,最终沉淀为此刻脚下的金砖与身上的衮服。
“诸卿,平身。”他的声音响起,低沉而浑厚,带着一种金铁摩擦般的质感,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
百官依序起身,垂手肃立。殿内再次陷入一片沉凝的寂静,唯有烛火燃烧的噼啪声和殿外呼啸的风声。
李善长深吸一口气,手捧一卷以明黄锦缎装裱的奏疏,出列上前,再次躬身,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臣李善长,率文武百官,万民之望,再拜恳请大王!”他展开奏疏,朗声宣读,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敲击:
“……自胡元失道,神器蒙尘,海宇鼎沸,生灵涂炭。大王起于布衣,提三尺剑,拯溺救焚,廓清江表。鄱阳一战,殄灭伪汉巨寇;洪都孤城,彰显忠义肝胆;安丰救驾,大义昭然天日!今应天根基己固,江南黎庶归心,此诚天命所钟,人心所向!臣等昧死百拜,伏乞大王上应天命,下顺民心,即吴王位!建百官司属,明章服,定礼乐,以安社稷,以定乾坤!此乃万民之幸,江山之幸!伏惟大王圣裁!”
话音落下,整个大殿的空气仿佛被瞬间抽空!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钉在丹陛之上那个玄色衮服的身影上。
朱元璋沉默着。时间仿佛凝固。冕冠的玉藻遮挡了他的眼神,无人能窥见那深陷眼窝中此刻翻腾的是何等风云。他缓缓抬起右手,那是一只布满老茧、骨节粗大、曾握过讨饭碗、更握过滴血钢刀的手。手指轻轻拂过蟠龙金椅冰冷的扶手,动作缓慢而充满力量感。
终于,他开口,声音依旧低沉,却带着一种开天辟地般的决断:
“元璋……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赖诸卿戮力同心,将士浴血效死,江南父老拥戴,方有尺寸之地,稍安黎庶。然……”他话锋一转,语气陡然沉凝如铁,“元室未灭,张寇(张士诚)犹存,北虏尚在!天下未定,生民犹在水火!此非高居王位、安享尊荣之时!”
百官心头一紧,呼吸都为之一窒。
朱元璋的声音陡然拔高,如同惊雷炸响,带着一种席卷天下的磅礴气势:
“然!诸卿所言,顺天应人,以安社稷,亦是至理!为拯斯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承天景命,元璋……不敢固辞!”
他猛地转身,玄色衮袍在烛光下划出一道威严的弧线,稳稳落座于那象征着江南至高权柄的蟠龙金椅之上!
“自今日起,建百官司属!立中书省,总摄机务!置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设大都督府,掌天下兵马!立御史台,纠劾百司!其余六部、诸司、卫所,皆依制设立!”一连串的命令,如同连珠炮般从朱元璋口中吐出,清晰、果决、不容置疑,瞬间勾勒出一个崭新王朝权力机器的雏形!
“臣等——领旨!吴王千岁!千岁!千千岁!”山呼海啸般的叩拜声再次响彻大殿,带着劫后余生般的激动与终于尘埃落定的狂热!
朱元璋端坐王位,冕旒微动。他的声音穿透欢呼,带着一种奇异的、双轨并行的威严:
“然!小明王韩林儿,乃宋室正统,抗元共主!其玺绶诏令,犹在滁州!故,凡我西吴境内,仍奉龙凤正朔!凡王命所出,皆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为凭!”此言一出,殿内瞬间安静了几分。李善长、刘基等人眼中精光一闪,瞬间领会了这“奉龙凤正朔”背后的深意——大义名分,人心所向,羽翼未丰前的韬光养晦!
“臣等谨遵王命!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同尊并奉!”短暂的沉寂后,是更加响亮的应诺。这“双轨并行”的诏命,如同最精密的榫卯,将新生的王权与旧日的法统巧妙地嵌合在一起。
当第一缕真正的晨曦刺破云层,艰难地穿透应天冬日厚重的寒气,洒在帅府——如今己是吴王宫殿——新漆的朱门上时,沉重的殿门缓缓开启。文武百官鱼贯而出,脸上犹带着朝贺的潮红与肩负新命的凝重。寒风扑面,却吹不散他们心头那团被新王点燃的火焰。
殿内,炭火依旧旺盛。朱元璋屏退了左右侍从。他缓缓站起身,走到巨大的雕花窗棂前。玄色衮服上的蟠龙在晨光熹微中显得愈发威严深沉。他伸出手,指尖触碰到冰冷的窗棂,目光穿透庭院中尚未化尽的残雪,投向东南方向——那里,是姑苏,是张士诚的“东吴”。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捻了捻衮服厚重华贵的锦缎袖口。触手温润,是顶级的苏杭织造。然而,在这华服之下,贴身之处,依旧是那件洗得发白、沾染过无数征尘与血火的——靛蓝布袍。粗糙的质感透过里衬传来,如同烙印在皮肤上的记忆。
“张士诚……”朱元璋的嘴唇无声地翕动,深陷的眼窝里,冰封的湖面下,是足以焚毁整个东吴的熔岩在奔涌。那件仓促织就的龙袍,那夜夜笙歌的平江王府,此刻在他眼中,不过是冢中枯骨前的最后一场迷梦。
“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他低声重复着这八个字,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带着铁腥味的弧度。这八个字,是盾,更是矛!是此刻立足江南的根基,更是未来刺向所有敌人的锋刃!
应天城头,寒风依旧凛冽。一面崭新的大纛在钟山之巅猎猎升起!玄色为底,一条狰狞矫健的金龙昂首腾跃,龙睛以赤色点染,仿佛燃烧着不灭的火焰。大纛边缘,一行小字在风中招展——西吴!
这面旗帜,迎着姑苏方向吹来的、带着脂粉与丝竹余韵的风,稳稳地扎根在江南的腹心之地。旗帜之下,是冰冷的刀枪,是充盈的府库,是无数双被“吴王令旨”凝聚起来的、燃烧着野望的眼睛。应天的寒钟己然敲响,宣告着一个属于“西吴”的时代,正式拉开了它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序幕!而东吴那醉生梦死的暖阁,又能抵挡这北来的寒潮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