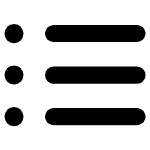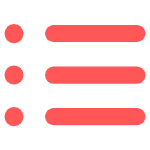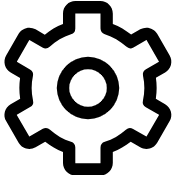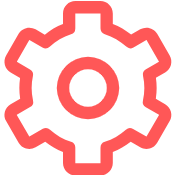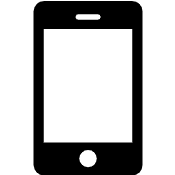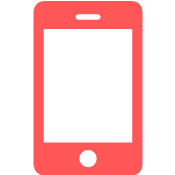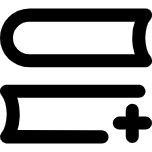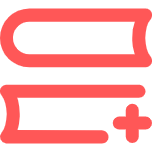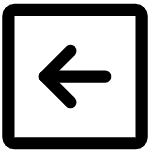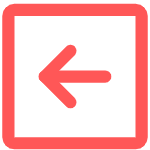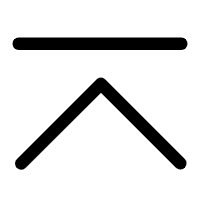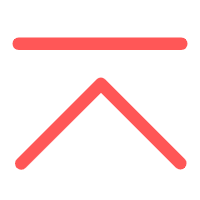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24章 礼贤馆中问鼎声
应天城西校场上,胡三舍溅落的血污尚未干透,那浓重的铁锈腥气在肃杀的秋风中盘桓不去。然而,应天的心脏——钟山脚下的帅府深处,却己悄然流转着另一股截然不同的气息。青烟缭绕,墨香氤氲,一种深沉而浩大的文脉,正试图涤荡这乱世的戾气,悄然勾勒着未来的轮廓。
城东,秦淮河畔一处清幽开阔之地,数日之内,数座轩昂雅致的馆舍拔地而起。粉墙黛瓦,飞檐翘角,与周遭肃杀的军营、繁忙的衙署迥然不同。门楣之上,悬一块新制的巨匾,三个漆金大字在秋阳下熠熠生辉——**礼贤馆**。大门敞开,迎候的不是刀剑甲胄,而是身着儒衫、头戴方巾的文士。他们或风尘仆仆自远方投奔,或己在应天观望多时,此刻被这“礼贤”二字所昭示的郑重,牵引着步入其中。馆内庭院深深,花木扶疏,设有精舍供宿,书斋藏万卷,更有敞轩供清谈论道。往来仆役皆轻手轻脚,言语恭谨,侍奉茶水笔墨,无微不至。这并非寻常驿馆,分明是朱元璋为天下才智之士筑起的一座精神殿堂。
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至江南乃至更远。那些在乱世烽烟中流离失所、或隐于山林、或屈身草莽的读书人,眼中渐渐燃起异样的光芒。应天,不仅以刀兵强横,更以“礼贤”之名,向天下昭示着一种迥异于草莽枭雄的气象。
深秋一日,礼贤馆最深处一间临水的静室。窗外残荷听雨,室内暖炉生香。朱元璋褪去了靛蓝布袍,换上一身素净的深色常服,端坐主位。他对面,坐着一位年过五旬的老者,清癯瘦削,须发己见斑白,唯有一双眼睛沉静睿智,透阅世情。此人正是名重东南的儒士,唐仲实。他曾亲历元廷鼎盛,亦目睹其江河日下,如今避居乡野,此次被朱元璋以极为恳切之礼,三番延请,方才至应天。
香茗的热气袅袅上升。朱元璋亲自执壶为唐仲实续水,姿态谦和,全无半分战场上杀伐决断的戾气。他放下茶壶,目光恳切地望向老者:
“仲实先生,元璋出身寒微,起于草莽,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大法,所知甚浅。”他的声音低沉而坦诚,“如今天下板荡,群雄逐鹿,元廷失鹿,神器蒙尘。元璋虽不才,亦知欲拯黎民于水火,非徒恃刀兵之利。故冒昧请教先生:昔日汉高帝提三尺剑,诛暴秦、灭强楚,终定鼎长安;汉光武起于南阳,昆阳一战摧莽军,光复汉祚;唐太宗扫平群雄,贞观之治垂范后世;宋太祖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开三百年太平基业;乃至本朝世祖皇帝(忽必烈),铁骑南下,混一寰宇。此数君者,皆雄才大略,开一代新天。先生学贯古今,洞悉兴替,敢问其所以能定鼎天下、开创皇朝者,根本之道,究竟何在?”
这番问话,开门见山,首指核心。唐仲实执杯的手微微一滞,抬眼看向朱元璋。这位布衣统帅深陷的眼窝里,此刻燃烧的并非战场上那种摧毁一切的烈焰,而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炽热的渴求——对“道”的渴求,对开创一个崭新秩序的渴求!这绝非寻常割据枭雄的野望,其志己昭然若揭!
唐仲实沉吟片刻,室内只闻窗外细雨沙沙。他缓缓放下茶盏,声音平和却带着金石之音:
“明公此问,关乎天命人心,非一言可蔽。然以老朽浅见,诸先帝能成不世之功,其道虽异,其本归一。”
“哦?请先生详述。”朱元璋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灼灼。
“其一,在顺天应人。”唐仲实手指轻叩桌面,“秦政苛暴,天下苦之久矣,故汉高‘约法三章’入关,关中父老箪食壶浆;王莽篡汉,倒行逆施,光武以‘复高祖之业’为号,人心思汉;隋炀无道,民怨沸腾,唐公(李渊)晋阳起兵,应者云集;五代离乱,武夫当国,生灵涂炭,宋祖以仁厚收将士之心,方有陈桥之变,兵不血刃而入汴梁。元世祖入主中原,亦行汉法,尊儒重道,以安天下。此数君,其兴也勃焉,皆因其所行,顺乎天理,应乎民心,解民倒悬,故能得道多助。”
朱元璋凝神静听,微微颔首。
“其二,在知人善任,总揽英雄。”唐仲实续道,“汉高有萧何治国、张良运筹、韩信将兵;光武云台二十八将,皆一时之杰;唐太宗凌烟阁上,房谋杜断,李靖英卫;宋祖麾下,赵普、曹彬、潘美,文武并用。便是世祖皇帝,亦重用刘秉忠、姚枢、许衡等汉人名臣,参决机要。明公试想,若无此等股肱栋梁倾力相辅,纵有盖世之勇,焉能成就帝业?”
朱元璋的目光扫过静室之外,仿佛穿透墙壁,看到了礼贤馆中那些或伏案疾书、或慷慨陈词的身影。他沉声道:“先生所言极是。元璋当效法先贤,虚怀若谷,广纳群英,使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
“其三,在立纲陈纪,明法度,定根本。”唐仲实的声音凝重起来,“天下初定,百废待兴,百弊丛生。若无法度森严,纲纪整肃,则前功尽弃。汉高入咸阳,即收秦律图籍,萧何定律令;光武释奴婢,省刑法;唐太宗制《贞观律》,宽简持平;宋祖杯酒释兵权,收藩镇之权归于中央,此皆立国定鼎之基石。便是世祖皇帝,亦颁《至元新格》,虽未尽善,亦为稳定之需。法度行,则赏罚明,赏罚明则人心定,人心定则天下安。”
“立纲陈纪……”朱元璋低声重复,深陷的眼窝里光芒闪烁,似有无数思绪奔涌。他仿佛看到了应天城外新立的蠲免苛捐木榜,看到了校场上那柄滴血的鬼头大刀,更看到了未来一个庞大帝国运转所需的、森严而有序的脉络。
“其西,”唐仲实的声音带着一种洞穿历史的苍茫,“在深根固本,养民力以蓄王师之威!此点,明公‘高筑墙,广积粮’之策,深得其要。”他赞许地看向朱元璋,“汉高有关中天府为基,光武有河北河内之富,唐宗据太原、河东之险与实,宋祖得汴梁漕运之利。无深厚之根基,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纵有雄师百万,亦难持久。明公屯田兴水,府库充盈,此乃王霸之资也!”
这番话,如同醍醐灌顶,将朱元璋三年来的苦心经营,提升到了开国帝王“深根固本”的战略高度。朱元璋胸中激荡,豁然开朗。他猛地站起身,对着唐仲实深深一揖:“先生金玉之言,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元璋茅塞顿开!顺天应人,总揽英雄,立纲陈纪,深根固本——此十六字,当为我应天立国之圭臬!先生大才,万望不弃鄙陋,留馆参赞,元璋必以师礼相待!”
唐仲实看着眼前这位对自己执弟子礼、目光炽烈如火的布衣枭雄,心中亦是波澜起伏。此人出身微末,却气吞寰宇;手段酷烈,又能礼贤下士;更难得的是,其志己不在割据一方,而在开创一个崭新的皇朝!他沉默片刻,终于缓缓起身,郑重还礼:“明公雄略,志在天下,老朽残躯,若能为新朝气象略尽绵薄,敢不从命?”
窗外,秋雨渐歇,一缕难得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礼贤馆的青瓦粉墙之上,映照得那“礼贤”二字愈发璀璨夺目。
静室之外的回廊转角,刘基负手而立,静静听着室内传来的对话声渐渐低沉下去。他清癯的脸上无悲无喜,唯有一双深邃的眸子,映照着庭院中雨后初晴的天光。礼贤馆的墨香与远处校场若有若无的血腥气,在这位“再世张良”的感知中奇异地交融。
“顺天应人,总揽英雄,立纲陈纪,深根固本……”刘基心中默念着唐仲实总结的十六字,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洞察一切的笑意,“好一个朱元璋!菩萨心肠播仁政之种,霹雳手段立森严之法,礼贤馆中更问鼎天下之道……这应天城,龙气己成。陈友谅啊陈友谅,你的巨舰再坚,可能敌得过这汇聚而来的——天命人心么?”
他转身,目光投向长江上游那片阴云密布的天空。礼贤馆的问鼎之声,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终将与上游压城的惊雷轰然相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