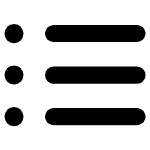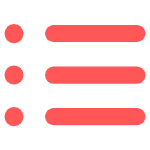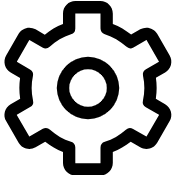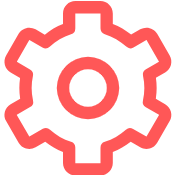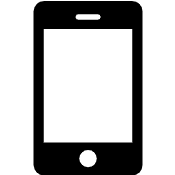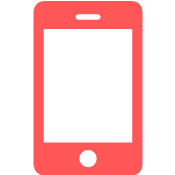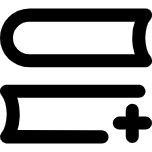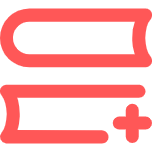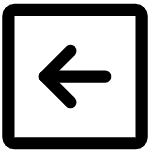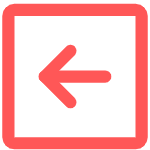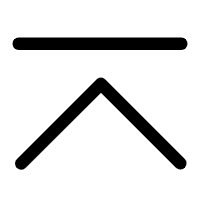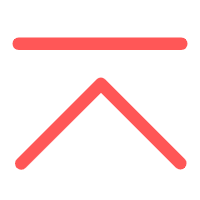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18章 应天新章
集庆城头,“朱”字大旗猎猎招展,撕裂了元廷统治江南的最后一片阴霾。硝烟尚未散尽,焦糊与血腥气依旧在街巷间浮动,但这座六朝金粉之地的心脏,己换了主人。
朱元璋策马行于应天(集庆更名)城中,靛蓝布袍洗得发白,与身后簇拥的甲胄鲜明的徐达、汤和、常遇春等人形成鲜明对比。他目光沉静,缓缓扫过街市:残破的屋舍,瑟缩在门板后惊魂未定的眼神,倒在街角无人收殓的尸骸,被劫掠一空的商铺……战争留下的疮痍触目惊心。他勒马停在昔日繁华的朱雀大道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抚平疮痍的沉定力量,穿透了死寂:
“传令!”
“即刻张榜安民!告谕全城百姓:朱家军吊民伐罪,除暴安良!凡我子民,各安其业,毋得惊疑!元廷苛政,一概废除!”
“开仓!放粮!赈济贫弱孤寡!凡家中断炊者,按丁口领取米粮!”
“设抚民官!巡查街巷,助民修缮屋舍,掩埋尸骸!凡有冤屈,可至府衙申诉,秉公处置!”
“严明军纪!重申‘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胆敢滋扰百姓者,立斩不赦!各营统军将领,约束部属,违者同罪!”
一道道命令如同温润的春雨,迅速渗入这座饱受摧残的巨城。士兵们不再是凶神恶煞的征服者,而是扛着粮袋走向粥棚的力夫,是帮着老人扶起倒塌门框的帮手。当第一锅热粥的香气在街角弥漫开来,当第一份写有“应天府抚民告示”的榜文被识字者念给惶惶的人群听,当看到几个因偷窃民财被当街正法的兵痞人头落地,应天城紧绷的神经,终于开始一点点松弛。麻木的眼神里,渐渐有了活气,有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新主“朱元帅”的名字,伴随着粮食与秩序,开始在劫后余生的百姓口中悄然流传。
就在应天城百废待兴、朱元璋埋首于无数繁杂军政事务之际,一队风尘仆仆、打着韩宋龙凤政权旗号的使者,在万众瞩目中进入了刚刚定名的应天府。使者高举小明王韩林儿的圣旨,在昔日江南行御史台那巍峨森严的大堂上,当众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枢密院同佥朱元璋,忠勇体国,克复集庆(使者仍用旧称),功在社稷!特擢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总制江南军国重事!望卿戮力王事,不负朕望!钦此——!”
“平章!”堂下侍立的徐达、汤和、常遇春等人,心头俱是一震!这可是行省最高长官,名义上掌控整个江南军政大权的显赫职位!小明王韩林儿(实为刘福通)的这份封赏,不可谓不重。这既是承认朱元璋攻占应天的功绩,更是试图用更高的名分,将这头日益强壮的猛虎,更紧地拴在韩宋的战车上。
朱元璋神色肃然,趋步上前,双手高举,稳稳接过那卷明黄帛书,动作一丝不苟,带着无可挑剔的恭谨:
“臣,朱元璋,叩谢天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俯首,额头触地。堂上诸将,包括桀骜如常遇春,也随着主帅的动作,齐刷刷拜倒,山呼万岁。场面庄重,礼数周全。
然而,当朱元璋抬起头,捧着那象征“江南行省平章”权柄的圣旨起身时,他深陷的眼窝里,却是一片冰封的湖面,不起半分波澜。那“平章”的虚名,并未在他眼底点燃丝毫真正的敬畏或狂喜。他目光扫过堂下众将,扫过这座刚刚被他更名为“应天”、视为帝王之资的雄城,心中只有朱升那九字真言在轰鸣:“缓称王!”这“平章”之位,不过是借来的一件华服,一件暂时遮蔽锋芒、积蓄力量的护身符。
当夜,应天城内原集庆路总管府衙署(规格低于行御史台,更显务实),灯火彻夜未熄。此处己被悄然更换了匾额——**“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匾额厚重,墨迹淋漓,透着一股新生的、不容置疑的威权。
大堂之内,气氛凝重而炽热,迥异于白日接旨时的表面恭顺。朱元璋踞坐主位,靛蓝布袍依旧,但气势如山岳。他面前摊开着应天及周边州县的详图,李善长、徐达、汤和、常遇春、俞通海、廖永安等核心班底肃立两侧。
“小明王之封,乃虚名羁縻。”朱元璋开门见山,声音低沉而清晰,再无半分朝堂上的恭谨,“应天,方为我等根基!‘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即日起开衙理事!军政号令,皆出于此!”
他的目光首先落在廖永安身上。这位巢湖水师的豪杰,与俞通海一同归附,战功卓著,更难得的是性情沉稳,深谙水战之道。
“廖永安!”
“末将在!”廖永安抱拳出列。
“着你为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统军元帅!总领水陆诸军操演、城防布控、江防要隘!应天之安危,系于你身!务使军令如山,壁垒森严!”
“末将遵命!定不负大帅重托!”廖永安声音沉稳,眼中精光闪动。统军元帅之位,位高权重,足见朱元璋对其倚重与信任,亦是对整个巢湖系力量的安抚与整合。
接着,朱元璋的目光转向李善长。这位最早追随的谋士,己从太平府都事历练而出,愈发老成干练。
“李善长!”
“属下在!”李善长上前一步。
“着你为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左右司郎中!”朱元璋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托付,“总理府衙一切机要文书、钱粮度支、刑名律令、官吏铨选、屯田水利、抚民安境!应天乃至日后所得州府之内政民生,悉数由你统筹!此乃根本,万勿懈怠!”
“属下领命!肝脑涂地,以报大帅知遇之恩!”李善长深深一揖,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左右司郎中,实乃大元帅府行政枢纽,权柄之重,远非小明王朝廷的虚职可比。这是将整个后方根基,托付于他之手。
一道道任命随之颁下:
“徐达!辅佐廖元帅,协理军务,专司步军操演、战阵攻防!兼掌军纪督查!”
“汤和!负责军械营造、粮秣转运、营寨修葺!务必保障军需无虞!”
“常遇春!依旧为先锋元帅,统精兵驻守要冲,厉兵秣马,随时听调出击!”
“俞通海!为水军副元帅,佐廖元帅统辖水师,整饬船舰,巡弋江防,肃清航道!”
文武诸将,各司其职,齐声应诺,声震屋瓦。这座“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如同一个高效而精密的战争机器核心,开始全速运转。
散衙之后,朱元璋并未休息。他换回布衣,仅带两名亲随,再次悄然步入应天城尚显冷清的街巷。白日开仓放粮的粥棚还未撤去,几个老弱妇孺捧着空碗,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满足和对明日微茫的期待。一处被战火损毁的学宫旧址前,几个文吏正指挥工匠清理瓦砾。更远处,隐约传来士兵操练的号令声和金铁交鸣,那是廖永安、徐达正在整肃军伍。
朱元璋在一处新贴的告示前停步。告示是“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的安民榜文,旁边还贴着招募工匠、通晓农桑者、识字文吏的榜文。一个穿着破烂儒衫的瘦削中年人,正借着火把的光,一个字一个字费力地读着招募令,昏黄的光映着他眼中闪烁的微光。
“高筑墙…”朱元璋心中默念,目光扫过正在修补的城墙轮廓。
“广积粮…”鼻尖仿佛嗅到了远处粮仓新谷的微香,脑中想着李善长呈报的屯田方略。
“缓称王…”他抬眼,望向北方韩宋政权所在的方向,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身洗得发白的靛蓝布袍,嘴角掠过一丝极淡、极冷的弧度。
他转身,踏着青石板路,一步步走回那座灯火通明、匾额簇新的“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身后,应天城的轮廓在初春的夜色中渐渐清晰,这座以“应天”为名、被赋予了全新意义的巨城,在“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的号令下,正如同蛰伏的巨兽,在江南的腹地,悄然积攒着改天换地的力量。九字真言,不再是刻在舆图上的线条,而是化作了这座城池的砖石、田亩的沟垄、军士的号令和百姓眼中渐生的微光。龙己入海,潜鳞蓄势,只待风雷激荡,便要搅动九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