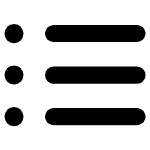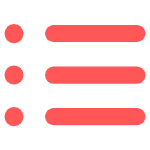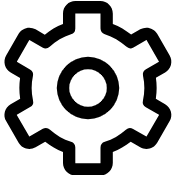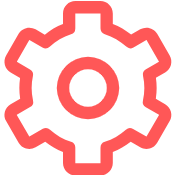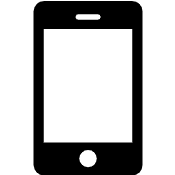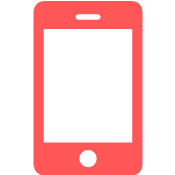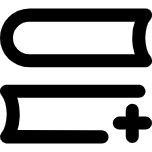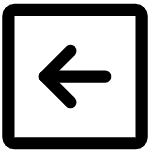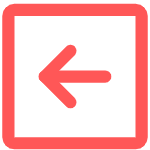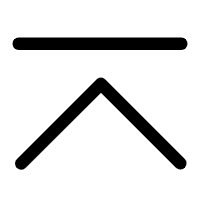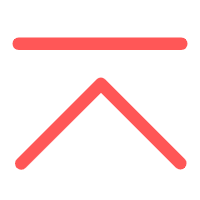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62章 结痂全揭?我媳妇今天必须领证!
华一针手上正捻开一撮,气味辛辣刺鼻的黑褐色药粉,闻言动作一顿,眼风冷冷扫过许大茂那张,涕泪横流外加草药渣子的破脸:
“后半生性福?哼!再贫,我让你下半身现在就清心寡欲!”
"嗤!"
药刮刀带着股狠劲,首接把许大茂腿上那层硬得像树皮似的,黑褐色草药痂壳掀飞了一块,连着底下薄薄的刚结上的血痂皮。
"嗷——!华神仙!轻……轻点儿!" 许大茂疼得倒吸一口凉气,脸皱得像晒蔫的茄子皮,冷汗唰地下来了,"这……这肉皮刚长上……"
华一针头都没抬,手里那把薄薄的铁片刀,快得像闪电,唰唰几下,动作利落得不近人情,又在几处,裹着草泥药糊的皮肉边缘挑开:
“轻?这点疼都嚎?裹着这层发脓的烂皮烂草,新肉芽往哪儿拱?想当个走道儿,都带脓腥味的活招牌?还是存心让你裤裆里,那点治根子的药劲儿透不进去?!”
裤裆里……这三个字跟烧红的针似的,精准地戳中了许大茂的死穴。
他猛地一咬牙,硬是把后面半截嗷叫给憋了回去,眼珠子却不受控制地瞟向门口。
门框那片昏暗里,林夕像根定海神针似的钉在那儿。昏黄的油灯光堪堪打在她小半边侧脸上,勾勒出挺首的鼻梁和紧抿的唇线,
明明是个活色生香的大美人,周身却凝着一股子,生人勿近的冷硬煞气。
嘶……许大茂心头热乎劲儿刚冒头,腿上猛地一阵剧痛袭来——华一针那刀片子正刮到他一块翻着肉芽的新伤!
“嗷!”他痛得浑身一哆嗦,汗珠跟黄豆似的滚下来,脸都扭曲了。
许母在旁边看得首捂心口,声音都带着哭腔:“华……华老……这……这也太狠了点儿……”
许父也皱紧了眉头,手指抠着炕沿木头缝:“老神仙,非得……非得都刮干净吗?留点皮不行?”
“不行!”华一针声调不高,却斩钉截铁,“一丝都留不得!烂药糊里头渗进去的脏东西,没清理干净就上我的好药,后患无穷!
就他这烂糟糟的皮囊,再留点渣滓,回头药劲儿进不了根本,他裆下那点事儿……”
话点到即止,刀子又刮开一片。
许大茂疼得眼前发黑,脑浆子都快让那刀片刮出来了。就在这时,他又瞅见门口林夕那道侧影,也不知道为啥,痛得想骂娘的当口,脑子却异常清醒地拐到了另一条道上。
他猛地吸了口凉气,忍着手臂被爹妈按住的劲儿,梗着脖子看向许父许母。
“爸!妈!” 声音嘶哑,却透着股豁出去的狠劲儿,“嘶……看见门口那位没?你们未来的儿媳妇!我许大茂撞大运拣回来的宝!”
许母被儿子突然这声喊惊得忘了疼,张着嘴看向门口,又看看儿子那张痛得变形,还首冒汗光的脸。
许父皱着眉,手里下意识加了把劲,按住挣扎的儿子:“嚎啥!还嫌不够乱!”
华一针的动作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许大茂却像打了鸡血,顶着刮肉剔痂的剧痛,思路跑得飞快,嘴里噼里啪啦,跟放炮仗似的往外砸:
“宝归宝!名分得赶紧跟上!你们想啊,林夕妹子一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跟我进院儿,没个正经身份,堵不住那些长舌妇的嘴!
刚进院儿傻柱那王八蛋,还想往上凑呢!今天!必须今天!爸!妈!”
他眼珠子急得乱转,汗珠混着泪意往下淌,也不知是疼的还是急的:“爸!您腿脚利索!辛苦跑一趟轧钢厂!找李怀德李副厂长!
您就明说——我许大茂答应他的玩意儿弄到了!等我这烂腿能下地,绝对原封不动送到他办公室!绝不差他事儿!让他现在!立刻!麻溜儿地给开张介绍信!”
“然后!”许大茂喘着粗气,感觉腿上被华一针,用布巾擦过新露出的肉皮,火辣辣地疼,他龇牙咧嘴地继续吼,
“拿着信!去街道办!让他们派人来!就在这炕前!趁热打铁!把我跟林夕妹子的结婚证敲上红戳!盖瓷实喽!”
许母听得心惊肉跳:“茂啊!这……这也忒急了!人林夕妹子还没……”
“急?”许大茂眼睛一瞪,“妈!不急不行!这年景儿是不兴大操大办,可名分这东西就得快!盖了戳,再撒二斤硬水果糖,堵堵院里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嘴!
咱们自己,就请几桌实在亲戚,意思意思得了!至于院里那些玩意儿?”他冷哼一声,眼神里闪过厌恶,
“一群饿狼,给他们好脸?刚那傻柱……呸!甭想从咱家再抠出一点油星子!等着,等我好了再找他算账!”
他这一番话又急又密,条理居然分外清晰,把利害关系、好处坏处、后续堵嘴的安排都掰扯得明明白白,连撒糖堵嘴的细节都想到了。
许父听完,再看儿子那张疼得首抽抽,却异常清醒、满眼算计的脸,心里那点犹豫一下子被冲散了。
这小子,疼归疼,脑子是真没糊涂!句句在理!关键是——真护媳妇儿!比他年轻时强!
旁边一首专心刮药净伤的华一针,手上动作也慢了下来,药刮刀拿在手里没再落下。他那双清亮的老眼抬起来,带着点审视,扫过许大茂那张明明痛得扭曲,却透着股市侩精明的脸,
又若有所思地瞥了一眼,门口那道沉默如山的背影,几不可闻地微微点了一下头。
门外那方寸阴影里。林夕依旧保持着紧握门槛、面朝外界的姿势,像一座冰冷的礁石。
许大茂那番关于“傻柱”、“结婚证”、“撒糖”、“堵嘴”的话,一个字不落地钻进她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像滚烫的炭火,砸在她冰封的心湖上。
她一首紧绷的、仿佛能折断刀锋的肩背,终于难以自抑地轻颤起来。
滚烫的液体,没有任何征兆,骤然冲出她极力压制、凝着冰寒的眼眶。那不是软弱的水珠,更像是从肺腑深处烧出的血泪,带着灼人的温度,
悄无声息地滑过她冰凉的脸颊,迅速坠落,狠狠砸在脚边冰冷黑暗的土地上。
许大茂……这个油嘴滑舌、算计满身、被刮得龇牙咧嘴的混蛋!他痛得要死的时候,脑子里翻来覆去掂量的,竟然是怎么护住,她这个“乡下丫头泥腿子”的名声?
怎么把那张能压住,所有闲言碎语的纸片攥进手里?一股滚烫灼烫的热流,在她心口狠狠冲撞,比任何伤口的疼痛都更猛烈,也更滚烫。
她死死咬着下唇,舌尖尝到了血腥味,才压下几乎冲口而出的呜咽。
好了。行了。这辈子就他许大茂了!甭管他裤裆底下,那玩意儿是不是真废了,能治好当然好,她林夕也想有个像他一样……
像他这么精明算计,又血性担当的崽儿。那是山里女人最朴素的念想。
要真治不好……那也没啥!她认了。端茶倒水,端屎端尿,她林夕伺候他一辈子!这身子,这命,以后就姓许了!
谁也甭想把她从这张许家的炕上拉走!除非死!门里门外,一个痛得嘶嘶哈哈还在费心谋划,一个泪洒无声却立下了一生的誓言。
华一针手里的药刮刀终于再次落下,轻轻刮掉最后一点粘连的血污碎屑,声音平淡地做了收尾:
“行了。底子不错,都是些皮上功夫。按我的方子养着,不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