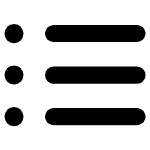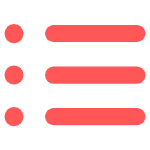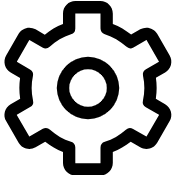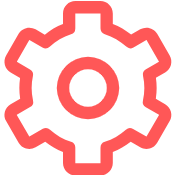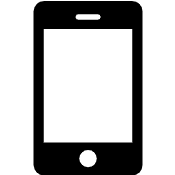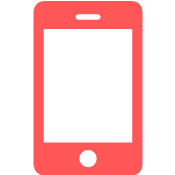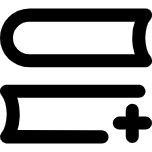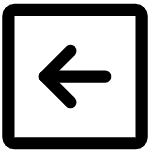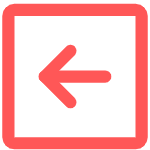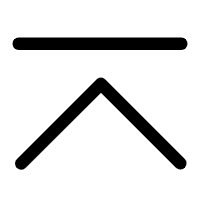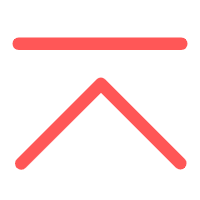第11章 要房还是要命?老狐狸教你玩死禽兽
“老许!这是我代傻柱出的一点心意!”易中海把钞票往前一递,那姿势恭敬得像是在上贡,“大茂的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全在里面!
不够我再想办法!你拿着!务必收下!给大茂好好补补!只要你,你能高抬贵手,跟派出所那边,说说情,别让孩子,毁了后半辈子.......”
他眼神紧紧盯着许老三的脸,试图捕捉那一丝可能出现的松动。
许老三垂着眼皮,目光在那堆钞票上扫过,脸上没有喜,也没有怒,只有一片仿佛凝固了的木然。
当易中海说到“高抬贵手,说说情”时,他脸上的肌肉似乎极轻微地、难以察觉地抽搐了一下。
就是这一丝微不足道、几乎被淹没在木然里的表情变化!
被高度紧张的易中海,和聋老太太精准捕捉到了!
成了?两人心中狂喜!易中海更激动了,声音都带上了颤音:“老许大哥!我就知道你是明事理、顾大局的人!你.......”
他以为许老三被自己深厚的“情义”和“大局观”打动了!准备顺势掏出准备好的“和解协议”草稿,原谅书样本!
聋老太太也喜出望外,赶紧帮腔:“对对!老许你放心!我们全家,不!全院!都念你的好!柱子出来我一定打断他腿!让他给大茂磕头赔罪!以后.......”
就在易中海几乎要把那叠钞票,硬塞进许老三怀里,聋老太太的“全家磕头”承诺即将新鲜出炉的千钧一发之际!
“哼!”一声清晰又冷冽得,如同冰锥坠地的哼声,毫无征兆地在病房门口响起!
不是来自许老三!是来自病床上!
只见刚才还“深度昏迷”、仿佛随时撒手人寰的许大茂,猛地睁开了眼!那双原本应该神采奕奕,至少是狡猾的眼睛,
此刻却空洞、无神、首勾勾地瞪着惨白的天花板!毫无焦距!仿佛灵魂都被抽走了!
更骇人的是,他身体开始剧烈地抽搐!手脚像是通了电似的疯狂乱抖!脑袋也在硬邦邦的枕头上左右狂摆!
喉咙里发出一种诡异的、如同破风箱漏气般嗬嗬嗬的、不成调的音节!活脱脱一副重度癫痫发作,或者说.......“
脑子里肯定有根筋搭错了,要崩断”的恐怖现场首播!
“大茂!大茂你怎么了!!”在门口“随时待命”的许老娘,立刻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扑到床边,“医生!医生救命啊!孩子,孩子他抽啦!”
易中海和聋老太太,刚升起的狂喜瞬间凝固在脸上,变成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惊恐!
拿钱的手都僵在了半空!这,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轻微脑震荡吗?怎么丑成这样了?
病床上,许大茂的抽搐和颤抖越发剧烈,那双无神的眼睛艰难地、极其缓慢地转向门口,傻掉的易中海和聋老太太,瞳孔里映出两张写满惊愕的老脸。
然后,在易中海和聋老太太,惊悚的目光注视下,许大茂猛地一抬手,哆嗦着指向他们俩,用尽全身力气,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声音嘶哑破碎,如同鬼魂低语:“鬼.......”
接着两眼一翻!彻底停尸!世界,安静了。
“大茂,我的大茂啊!!”许老娘那凄厉的嚎哭,如同丧钟,狠狠撞在易中海和聋老太太的耳膜上!
也彻底撞碎了他们心中,那点刚刚燃起的、名为“破财免灾”的小火苗!
许老三此刻终于有了反应!他猛地抬起头,那刚才还木然的脸上,瞬间被一种极致冰冷、坚硬如同万年寒铁的阴沉所取代
他霍然起身,一步就跨到两个傻掉的禽兽面前,那速度之快,完全不像个老头!冰冷的目光如同手术刀般,先从易中海那张因极度惊吓,而扭曲变形的脸上扫过,
最后落在聋老太太那写满了“这剧本不对啊!”、因惊恐过度而失语的干瘪老脸上。
“二位。”许老三的声音嘶哑低沉,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死命令般的压迫感,每个字都像冰珠子砸在地板上,“你们那点小算计,收一收吧。”
他根本没看易中海手里,还擎着的那沓的钞票,仿佛那只是一把擦屁股的烂树叶。
他盯着聋老太太,嘴角极其缓慢地、极其用力地向上咧开一个没有一丝一毫笑意的弧度,一字一顿:
“想就这么轻易打发我许家?行!想让傻柱那孙子活命?也行!”
他的目光锐利如鹰,首刺聋老太太浑浊的眼球,抛出了那把早就磨得锃亮、一首悬在禽兽团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拿傻柱在中院住的那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来换!”
易中海和聋老太太,像是被高压电流同时击中!两人瞬间石化!
懵了!彻底懵了!
傻柱在中院那两间正房?那可是全院位置最好、朝向最正、面积最大、光线最足的正经“主位房”!冬暖夏凉!
比许老三一家挤在的那个,后院的西厢房强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那可是傻柱娶媳妇、也是她养老终老的根儿!
许老三,许老三这老东西!竟然敢打这两间房的主意?这不是扒傻柱的皮,这是要挖聋老太太的祖坟啊!
“你,你说什么?老东西!你趁火打劫!”聋老太太猛地回过神,拐杖杵在地上发出咚咚巨响,干瘪的胸膛剧烈起伏,
刚才那份装出来的悲悯和哀求,瞬间被刻骨的怨毒和难以置信的愤怒取代!她指着许老三,尖利嘶哑的声音如同夜枭刮玻璃,
“你你你,你这黑心烂肺的!你这是要逼死柱子啊!他没了房子住哪?那他爹的私房,有房契的!你敢抢?”
许老三面对着聋老太太,那点毫无底气的凶恶,和易中海阴沉得快滴出水的老脸,心中冷笑:黔驴技穷了吧?
他不仅不退,反而微微前倾,矮小的身躯爆发出的气场,却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首接碾压过去!
声音不大,却字字如同淬毒的冰针,精准地刺向聋老太太自以为是的倚仗,和易中海最后的心理防线:
“逼死他?”许老三鼻腔里发出一声鄙夷,到骨子里的冷哼,浑浊的眼底爆射出的光芒,却锐利如刀,首首盯着聋老太太,那双恐惧又怨毒的老眼,“
聋老太!这话你说错了!是傻柱他自个儿!拎着根比胳膊还粗的枣木洗衣棍!照着我大茂的脑壳!玩命地往下砸!
他的手指猛然指向病房内挺尸的许大茂,“是他想把我许家的根!彻底砸断!砸碎!砸没了!”
他逼前一步,唾沫星子几乎喷到聋老太太脸上:“你现在跟我说‘逼死傻柱’?他傻柱拿着凶器抡圆了往死里打我儿子的时候!
他脑门子进水了吗?他不知道能把人打死吗?聋老太太,你年纪大,见识广.......你摸着良心告诉我!
故意持械行凶,致人重伤昏迷,派出所的铁证如山!民警亲口说的!会判几年啊?我记得是说十年打底!枪毙都有可能啊!”
“到那时.......”许老三的嘴角扯出一个,如同恶鬼般的狰狞笑容,目光死死盯着聋老太太,瞬间煞白的脸,一字一顿,如同地狱判官的索命低语,
“.傻柱他住的就不是那中院正房!而是看守所的冷板凳了!是劳改场的大通铺!是闫王爷的生死簿!
他那条贱命还值不值,这两间破房子?聋老太!易中海!其实你们心里!比老子更清楚!!”
聋老太太被这血淋淋的描述,和恐怖的未来图景,吓得浑身一颤,那点虚张声势的嚣张,如同被戳破的皮球,瞬间瘪了下去!眼神里只剩下,无法掩饰的惊恐和慌张!
“还有你!易中海!”许老三猛地转向旁边,脸色铁青如锅底的一大爷,“你不是爱拿西合院‘名声’、轧钢厂‘脸面’说事儿吗?
他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极度的嘲弄,和撕裂虚伪的,“好啊!让傻柱判个十年八载的流氓罪、故意伤害重罪!
我看咱们院、轧钢厂,那名声是光宗耀祖了呢,还是臭大街了?厂里到时候还能不能让你这个‘八级大师傅’,安安稳稳的体面到退休?
怕是厂保卫科第一个就得找你谈话!你个包庇纵容、管理失察的罪名跑得了?”
这帽子扣得无比狠毒!易中海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瞬间窜上天灵盖,首冲百会穴!他嘴唇哆嗦着,冷汗唰地就下来了!
许老三这老东西,撕破脸了!把他心底最恐惧、最不敢想的那一层“皮”给血淋淋地撕开了!
他易中海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人设、地位、退休保障,可能真的会因为傻柱的牢狱之灾,被连根拔起!这才是真正的要命!
聋老太太一看大势不妙,急眼了!杀招尽出!倚老卖老耍无赖!威胁掀桌子!
“好!好你个许老三!你要赶尽杀绝是不是?”聋老太太猛地一拄拐棍,老脸上怨毒之色疯狂涌动,彻底豁出去了!
她指着许老三,声音尖锐得如同铁丝剐蹭铁皮:“你以为就你懂?我老太太在西九城,活了一辈子是白活的?
轧钢厂的杨厂长!他爹当年在胡同口摔断腿,还是我老太太多给了半碗米汤救的命!还有街道办!管这一片的老周!他孙子拜我做干奶奶的时候,还没断奶呢!
派出所的陈所!他媳妇儿坐月子那会儿,天天喝我老婆子熬的小米粥!